�ż����x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Ŵ��ġ����@���ܴa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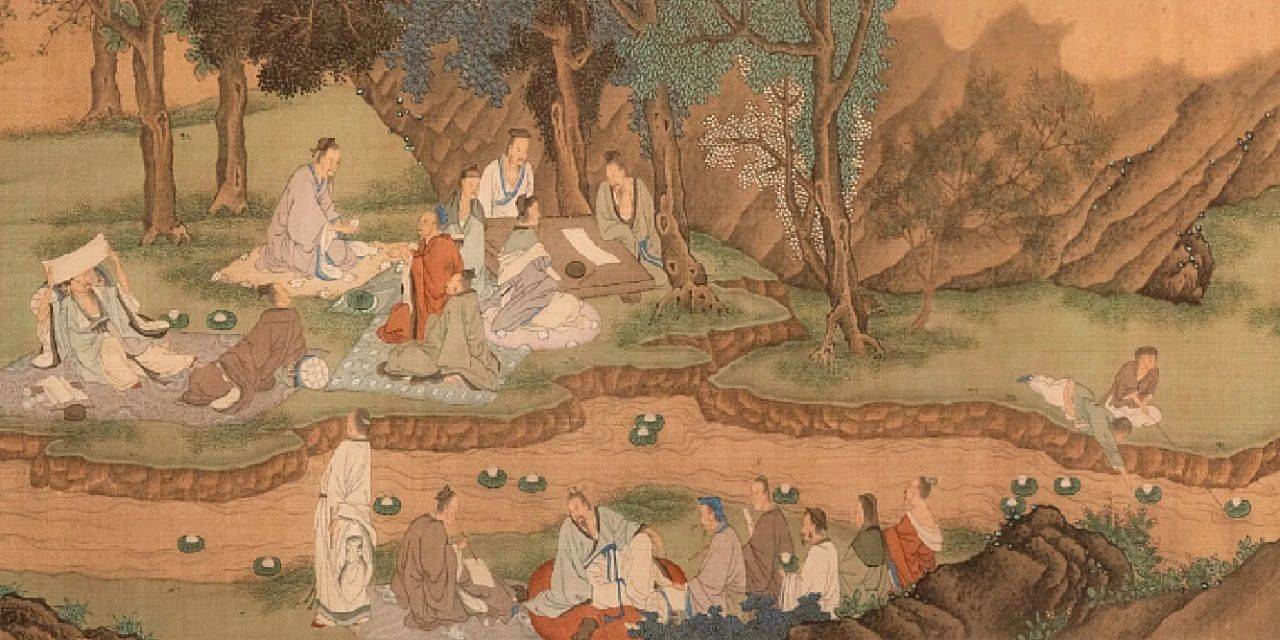
���Θ����g�c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옷�ı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ͬ�ӟ��ԡ��Έ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@���m�o�C(j��)е�b�����s��M�˄e�ӵ���Ȥ�c���¡�
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
ID | BMR2004
�Ϻ�����Ҳ̫�옷�˰���7��5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ߘ��@�ȼم^(q��)��ʽ�_�@�����˚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ᣬ�Ϻ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@�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g�c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옷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ݚvʷ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ͬ�ӟ��ԡ��Έ@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@���m�o�C(j��)е�b�����s��M�˄e�ӵ���Ȥ�c������
�Ŵ��Ї��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ʽ���ӣ��ʼҌmԷ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ٹ�ͬ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tƫ��˽�҈@�ֻ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�o�^�ĕr(sh��)׃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ڹ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M�@�о����A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҂�һ�ӣ����Έ@�Ќ������ĵķ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䐂���γ�ij�N��Խ�r(sh��)�յ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
01
������ʿ�ľە�(hu��)
�Ї��vʷ�ϵ��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貽Y(ji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Ї��Ŵ��S����ʵ��罻�c���e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�Ҳ��Ļ��ζ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̵��о��R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A�Čm͢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Ԋ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ĵĸ��žە?hu��)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ڌ��o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h(yu��n)�x�m�̵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cˇ�g(sh��)�Ľ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ɽˮ֮Ȥ�c���ĠI��֮���Ĉ@�֣���ɞ���d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ԓ]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x��ˮ��Ԋ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ֵ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鼤�l(f��)�`�С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ʹ�ż��ɞ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_�����`��Ԓ�c�Ļ�ʢ����
�Ї��vʷ�ϵ��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ҏ����ڡ��ĉ�Ӱ���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ǟo������֮�^Ҳ���e�t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e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t�ܽ����ѣ��e�t������e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҇��Ŵ����^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@�����V�{��ʿ��˾�R���硢ö�˵Ȳſ��L�ڼ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e�͡��ļ�Ԓ����ǧ�ţ���ס�ʮ�d�����@��֮���Դ�ڴ���ʷ�Q�����@֮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H���ܲ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ا����ֲ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ʿ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Єt�Bݛ��ֹ�t�Bϯ�������ھƺ�����֮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xԊ����ʢ�r��ǰ���Բ�ا���ġ���Փ��Փ�ġ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ĵ�Ⱥ�w���_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˼��F(tu��n)���ż����͵��Ⱥӣ���Ԋ�Ƴ����I(l��ng)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_�L(f��ng)�⡱�����x��(qu��n)��ʯ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Ȉ@���¹ڽ^һ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ټ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ȶ�ʮ���˽Y(ji��)�ɡ���ȶ�ʮ���ѡ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꣬ʯ���ڴ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xԊ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|�x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ڕ�(hu��)��ɽ��mͤ�ټ��x�����O�b����ʮ��λ��ʿ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Ⱥ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̼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x���x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d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ƪ���mͤ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c�����p�^��ʹ�mͤ�ż��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p�塣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ϡ���ˣ����ϕ�(hu��)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(hu��)Ⱥ�w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Ѯ����Ԫˬ��ɮ��M�����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Ԋ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gƽ����ʮ�q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(hu��)�Z��(d��ng)һ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ψD���Ԟ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ʷ�Ϫ�(d��)�صĸ��g�L(f��ng)�ł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N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ε���Ҫ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P(y��ng)�ݮ���䛡���ӛ���R��С�ᭇ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݈@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k�ż�Ԋ��(hu��)�Ķ�ʢ֮̎��ÿ���ż�֮�����@�и�̎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IJ��ã�ÿϯ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Ʒһ��(y��ng)��ȫ�����P��֧��īһ�V���˳�һ����ˮע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{���ď�����Ԋ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c��ʳ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ڹ����߷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岢�����ͳ��С���
�ڱ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Ԗ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ġ����@�ż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ɱ��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@�ż��D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v���g����R��Ԗ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Ո���K�Y���Sͥ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^��ʮ��λ��ʿ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}ʯ����ȸ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桰Ȼ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ĵ䷶��
���^ֵ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汱���īI(xi��n)�в��o�P(gu��n)�ڡ����@�ż�����ֱ��ӛ�d���@���l(f��)�ˌW(xu��)�ߌ����挍(sh��)�Ե�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f�ۂ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Ǻ��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Ԗ�c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_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Ԕ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˴��ż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īI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ߗ�ʿ���ڡ��|�O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_ָ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Ԗ��Ո?zh��)K�Y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˲ܰ������L�Z��Ҳ���Դ_�J(r��n)���ɴ˿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ͨ�^�īI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@���ż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䡰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λ���Դ˴_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Ļ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ż����ܴ�̶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v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D����
02
ƽ����յ��Θ�
�Ŵ���ͨ���յ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M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⾳��Ԋ�ĕ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ͬ���Ŵ���ͨ���յ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t��M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Έ@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q�r(sh��)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оo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ڳ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_�ſ��g���R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м����@��]�о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İ����ķ���ȡ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լ��MĿ��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ʳ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v�İّ��sˣ�Լ�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δ����Ї��Ŵ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δ��@�ֵ��dʢ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ٵĸ�����ʼ҈@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⣩�ĭ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Q�顰�_�ء���˽�҈@���༊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T��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ψ@����ˎʢ�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ͤ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^����
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ɟ��[���о�֮�����ʳ����Ҫһ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˳��Ԏ��ɼZ�痗䭅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о�ʳ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uС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硰����ɩ�~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еĊʘ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t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ӣ�˽�҈@�֞����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�⡢��ǧ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ϵ�ͨ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缯���c(di��n)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胺��Ů����M�@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У����۸��ɸ����^���Ƽ���ʢ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ͬǰ��һ����̤���δ��L(f��ng)��Oʢ���ɞ�ȫ���ԵĻ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ӳ�˕r(sh��)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γɡ�܇����ˮ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o̓�ա��ğ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Ұ���O(sh��)ϯ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ʎ��ǧ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~�Ȋʘ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S��Ů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c�g�����p��Ҳ���Έ@�ĺ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֮һ���δ��p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ĵ��ʢ�_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˷��ϔy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ǧ���˽�҈@�ֺͻ����ڻ��ڳ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��
�δ��Ĺ�(ji��)��c�䳣�Ժ��ġ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ʽչ�_���@�ֳɞ���dȫ��g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Ԫ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Ԫ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Ĉ@�֟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͢�����ּ��ʼ҈@���b�c(di��n)�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ّ����[�[���С����γɾd��ʮ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c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_�ŵĻʼ�Է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Z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ّ��ڟ����x�͵Ĉ@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ҹ֮�g��
��ʳ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翗���˕r(sh��)˽�҈@���c��Ұ���ټ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γɴ��ʹ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ڈ@��ɽҰ�g̤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~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ٲݡ��Ȟ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ػʼ҈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kʢ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ʮ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۸��ɊZ��(bi��o)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Ŀ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Έ@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߃����͢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I�u���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ﳣ����ͬ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ճ��Ąt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R�۟o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s���ˡ���ָ��Ԫ�r(sh��)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ܴa�^�ļ�ˇ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ܑ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~�ȣ��(xi��ng)Ŀ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Ŀ��Ͼ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ľC�����Θ��@��
03
�Έ@�c�B(y��ng)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p�ĺ��ăr(ji��)ֵ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^�pɽˮ��ľ�Ȍ�(sh��)�w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ζ�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
�mȻ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Ⱥ�в�ͬ���Έ@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𪣨���T��ʮ���t֮һ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(xi��ng)Ŀ�;�ɫֻ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龰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҂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Ŀɫ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Լ��Č�Ԓ��
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Ϲ��ڡ����ȳˡ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@��֮����Ω��ɽ�c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@�֕r(sh��)����Ҫ�^�[�ı���ɽ��ˮ�B(t��i)֮�����Ї��ŵ�@���е�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͈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�}��ˮ֧֮���Գ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ұ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f���@��ɽˮ���Գ���Ȼ֮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v�挍(sh��)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@�ց��f���侰� I��t��Ҫ��ه��ɽ��ˮ���v����һ�״�ˮ��һȭ��ɽ�����ԘO����ˮ���cȭʯ�������Եر��F(xi��n)ɽˮ��Ȫ�ğo�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@���O(sh��)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ʯ���˹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@��ˮʯ����ɟo����һ��t̫�Aǧ����һ�ׄt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ıȔM�c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ʹ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֮���|�l(f��)�S���Č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Ķ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Ȼɽˮ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Ȥ��
�Έ@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S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Έ@�r(sh��)�п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ڈ@�С�����̼t�_�顱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ʮ�ġ�˼�t�wӛ���tӛ�d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ľ�����IJ�ͬ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аٻ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s�G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ï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ȻԪ������ͬ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̵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p�ĺ��ăr(ji��)ֵ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^�pɽˮ��ľ�Ȍ�(sh��)�w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ζ�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�@�N��Ӵε����}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Ӱ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γɵġ��L(f��ng)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Ϧ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?du��)I��ğo߅�⾳�팍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¾��m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s�ܞ�@�־��^ע���S���ČӴ��c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Ҫ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c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(li��n)�ķ�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|��ȥ�w�(y��n)��һ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ʷ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ǽ^�����C��һ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ͤ�p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¡��Fڡ��X�����c�ơ��cɽ���cˮ������һ�ס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L��һ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ͤһ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桱�������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nãѩ���ĺ���µõ��O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L(f��ng)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(d��)���⾳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Έ@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̵���˼�c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Έ@֮�С�
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Έ@���Ŵ���Ҳ�г���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ʵ۾��e�k�^�����}�Έ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ͨ���յĄ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ӱ��njm͢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Ĵ���ġ��I�u�֡����@�l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ֵ��O(sh��)�ڈA���@ͬ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Ι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䁡��c(di��n)�Ĕ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y��ng)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؛���լ��M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߽Ԟ�m��(n��i)̫�O(ji��n)���mŮ������߀�д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һ׃���ɞ�ߺ�Ƚ��u���ƹ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Ļ�Ӌ(j��)��ӑ�r(ji��)߀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о�ٵ�Z�����̽��u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ӂ��t�d�°�Ȼ�ػ������ο͡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Ӌ(j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d�µ����x��Ʒ��Ʒ�L���^С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ɷ�н��µ��h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)�f��r(ji��)Ҳ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ף�һ���X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һ������ʵ�ҲҪ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ء����~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ͽ�ɫ�����Α�����ӌm���Ľy(t��ng)���ߵ��Զ̕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НM�㌦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
�oՓ������ɽˮ��Ʒζ��ȭʯ��߀�Ǹ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Έ@�ľ���K�w�����`�ĺ��B(y��ng)�c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R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ɫ�D(zhu��n)�Q�У���Ԓ��(n��i)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ã�����Ҳ�T���옷�ĺ���ʼ�K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g�c׃�Q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|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ů��(li��n)�Y(ji��)�c���ҵİ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
��Դ | ���̌W(xu��)Ժ���s־7�¿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1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