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Ľ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(g��u)
ժҪ
�������1555�C1636���c�w���\��1254�C1322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�ʷ�ϵľ���(du��)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Ԫ��֮�H���˕��L(f��ng)��׃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�u(p��ng)Փ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B(t��i)�ġ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귴˼�䡰���ġ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֮�I������t�ڸ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挍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Գ�Խ���@һ���M(j��n)܉�E���H��ӳ�˶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ij����^�̣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w��С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wϵ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Փ�wϵ���P���J(r��n)֪�c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S���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ˌ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ij�Խ���ԡ��ϱ���Փ���ؘ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ʷ�Vϵ���ԡ����㡱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⡱ȡ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ؚw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ĵĂ�(g��)�Ի���Փ�wϵ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_�¡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Խ��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(l��i)�_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λ�ĵ��͙C(j��)����
�P(gu��n)�I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Խ���ϱ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(g��u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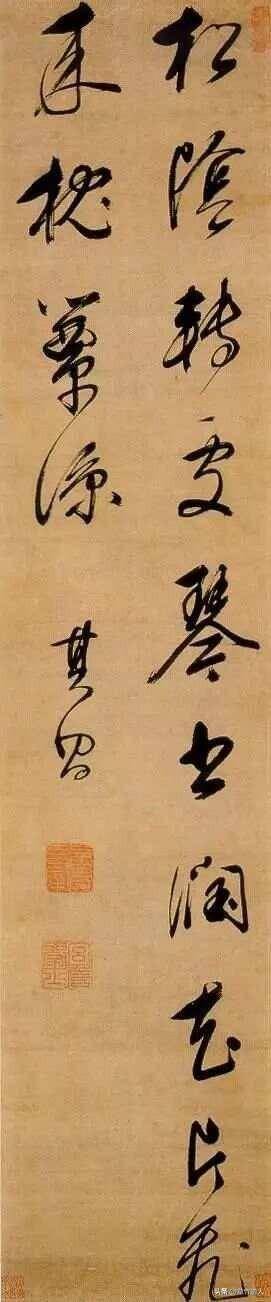
һ�����ԣ�?ji��n)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c�о�ҕ��
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ˌ�(du��)ǰ�t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P(gu��n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Ҷ�λ�c��Փ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�u(p��ng)Փ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F(xi��n)��ĵ��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ţ��ԡ��x���L(f��ng)퍡��C�����Ε��L(f��ng)֮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ĈA�족��Ӱ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Ԟ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đB(t��i)�Ȳ���һ��؞֮�����dz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A����׃���c��(n��i)�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Q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ʮ�꣬ʼ���E���w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S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ˑB(t��i)�q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DZMʧ�������Rġ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Ɂy�桱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ì�ܵ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t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һ�l�����ij��L(zh��ng)�c��Խ·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ġ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Ǻ�(ji��n)�εđB(t��i)�ȓu�[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ġ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Խ��ͨ�^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˂�(g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�͑׃������˴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�ʷ�еĪ�(d��)�ص�λ�����Č��ĕ�Փ�wϵ���P���J(r��n)֪�c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S����ϵ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ij�Խ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ԡ��ؚw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ĵĕ�����Փ�wϵ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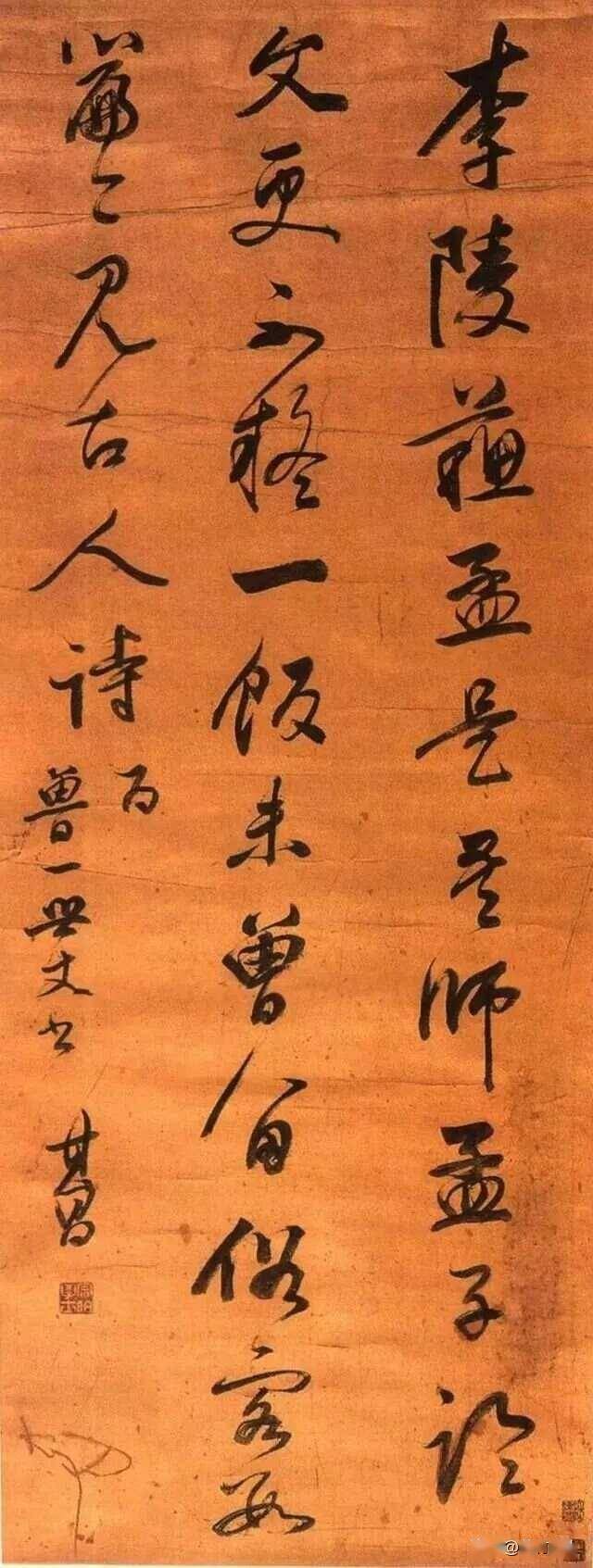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ČW(xu��)��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ȡ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Ա�ҕ�顰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䷶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e������̹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w������Ҋ�w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wϵ�еĺ��ĵ�λ��
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ġ��Ҫ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ׂ�(g��)���棺
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ȡ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(y��n)֔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Ό��b���M��(sh��)��չ�����Џ�(qi��ng)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硶�Е��R�w���\ǧ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ڽY(ji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u�w�ϱ֮ⷽò���M��ȡ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(w��n)��
�P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ùP�A��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W(xu��)�A����ע�عP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c���A�족���䡶�R�w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B؞�����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ͬ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(f��)�š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顰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x���K�w�³ˡ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ԕx�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һ�A�ε�ġ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պ��׃��춨�ˈ�(j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W(xu��)�̫�����^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˵��w���d����ʼ֪�����ùP֮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ɞ���ͨ��x�ƽ�(j��ng)��ġ��н顱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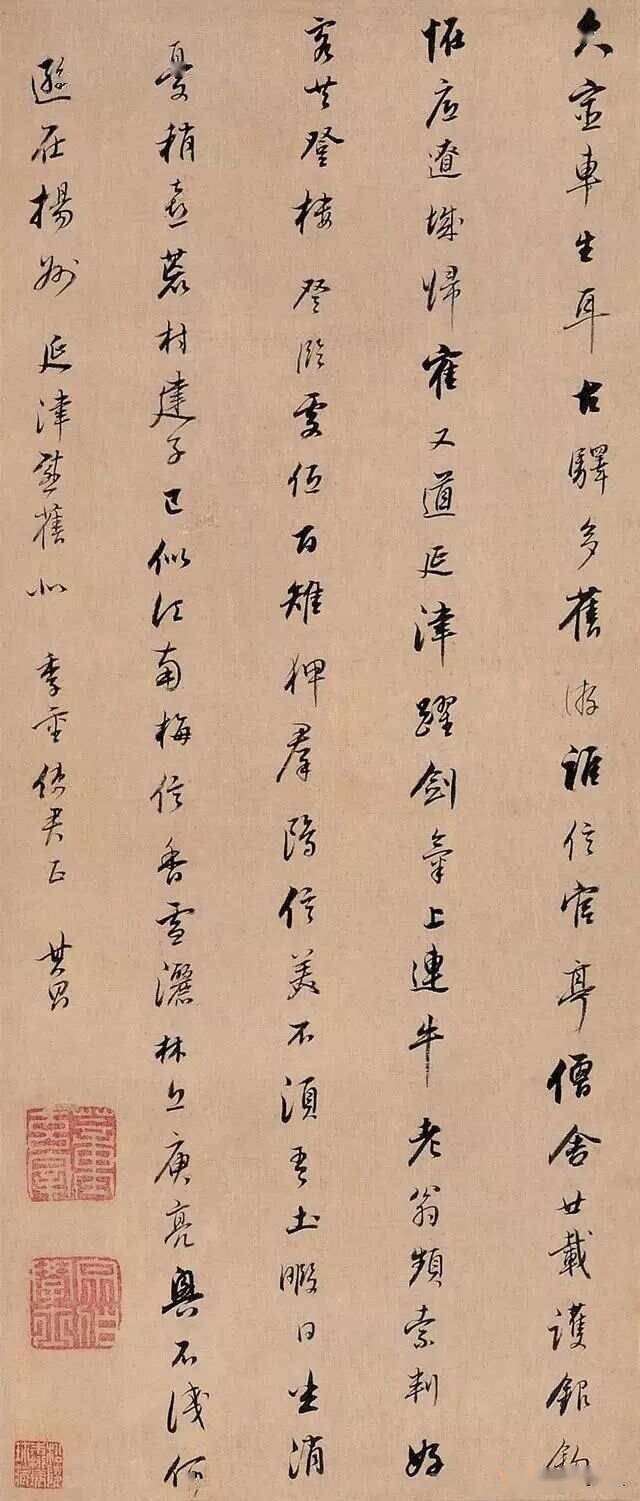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ġ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
Ȼ�����S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(g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Ȱ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˼���@һ�D(zhu��n)׃��s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qǰ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څ�ڳ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t�ס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Ȥ�c���ݚ⡱֮����
�ڡ����U���S�P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_(d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
�����ڕ��ƿ�ֱ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
���Z(y��)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Լ��ڼ����Ͽ��c�w�ϱ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족���ԡ���ɫ���^(q��)�e���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@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裬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㡱��ָһ�Nδ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¶�ĹPīȤζ�������족���tָ�^���쾚��(d��o)�µij�ʽ���c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Ěvʷ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ĽǶ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w���ġ��L(f��ng)�ǡ���
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ԁ�(l��i)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E����֮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ل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Փ����Ʒ�c��Ʒ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m�е����u(p��ng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㡱�Č������ޡ��@�N��˼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ٝM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ġ�Ӱ�ӡ�����ԇ�D�ھ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c֮���_���x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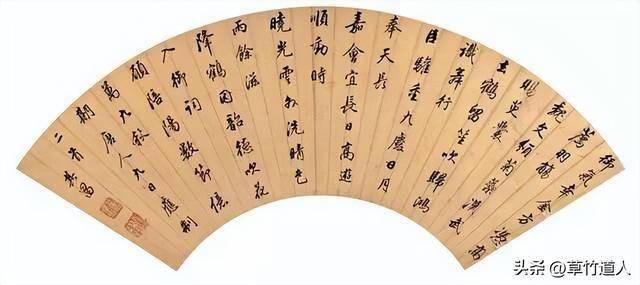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Խ֮һ����Փ�wϵ���ؘ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(f��)�š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ij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ڕ�Փ�wϵ�Ľ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ĕ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(f��)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t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ͽȡ���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(du��)�x�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Ҍ�(sh��)�^�����@һ·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ģ��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ڴ˻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ϵ�y(t��ng)���c�܌W(xu��)��ȵġ��ϱ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M�ܴ�ՓԴ�ڮ�ʷ������߉��ȫ�m���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֞顰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ˮ�/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Ժ�w��/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ǰ���ء��D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u�ޡ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䡢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w�롰���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
ͨ�^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ˌ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Փ���ij�Խ��
�ġ��W(xu��)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c�Ş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顰�R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^���eֹЦ�Z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ϡ�
�ġ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U���S�P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tֱ�ʶ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ɡ��Ǽ��g(sh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ǡ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ڼ��˼ѡ�����Ȼ��B(t��i)��
�����µ�ʷ�W(xu��)�Vϵ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ϱ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^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λ�顰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ǡ��_��(chu��ng)�ߡ����Ķ��ڕ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д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y��u)�ȵ�λ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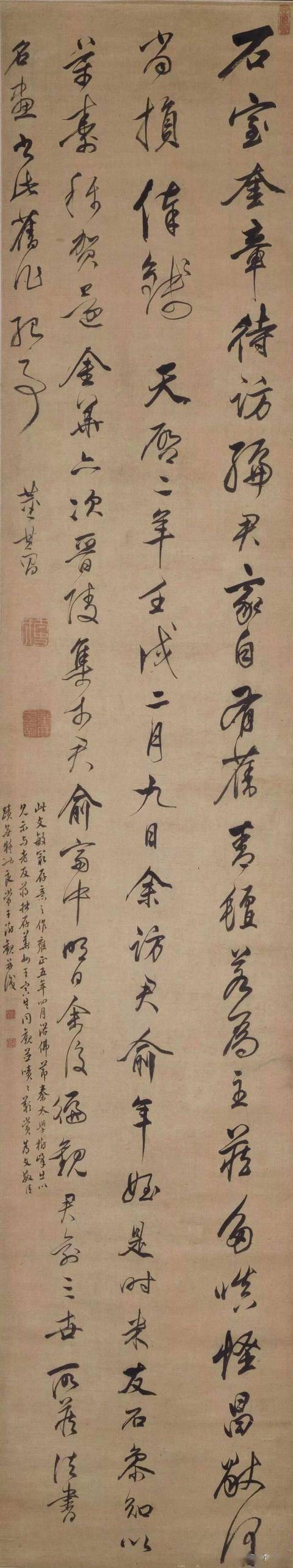
�塢��Խ֮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J(r��n)֪�ĸ��¡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㡱
�ڹ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ˌ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�ֱ�ӌ�(du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ԡ��족���ġ����Q���ùP�A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ᰴ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Q���O���^�p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족��(d��o)�¡��ס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ζ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㡱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ᰴ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P�p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ᰴ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ּ�(x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p���D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A��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硰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⡱�c��żȻ�ԡ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ڼ��˼ѡ��� spontaneity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ݹP���qī�ȡ����⡱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
�ԡ���ī���ơ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Ý�ī��ɫ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õ�ī���γɡ���ī��퍡��Ī�(d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c�䡰���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
�@�N�P�����£�ʹ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ҕ�X���c�w���\���_���x���w���硰���P�ز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ơ�ˮī���⡱���w���硰�R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硰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족���ԡ��㡱�^(q��)�e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˹P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ؘ�(g��u)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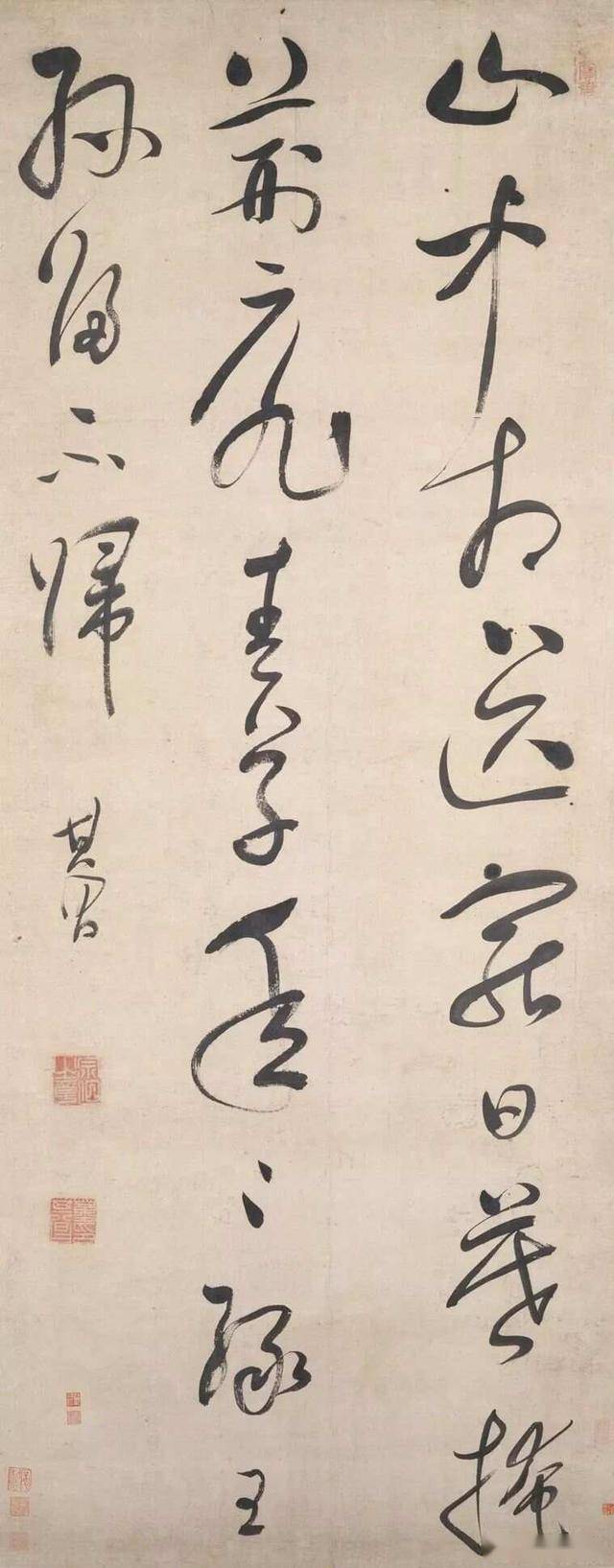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Խ֮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
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挍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ˌ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ĸ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w���\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(f��)�w�x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Ļ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Џ�(qi��ng)�ҵ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c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Ե����ɱ��_(d��)��
�@�N���ؚw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ڣ�
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(g��)�ԡ��c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顰���S���Y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ǧ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һ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O�߱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ע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顰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ƺ�ҹ�����o�r(sh��)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B(t��i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B(y��ng)�ԡ�֮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Ǽ�ˇ�����ǡ��B(y��ng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U���S�P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öU�Z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֮�£��w���\�ĕ�����ƫ��ˇ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顰���ԡ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@�N�ġ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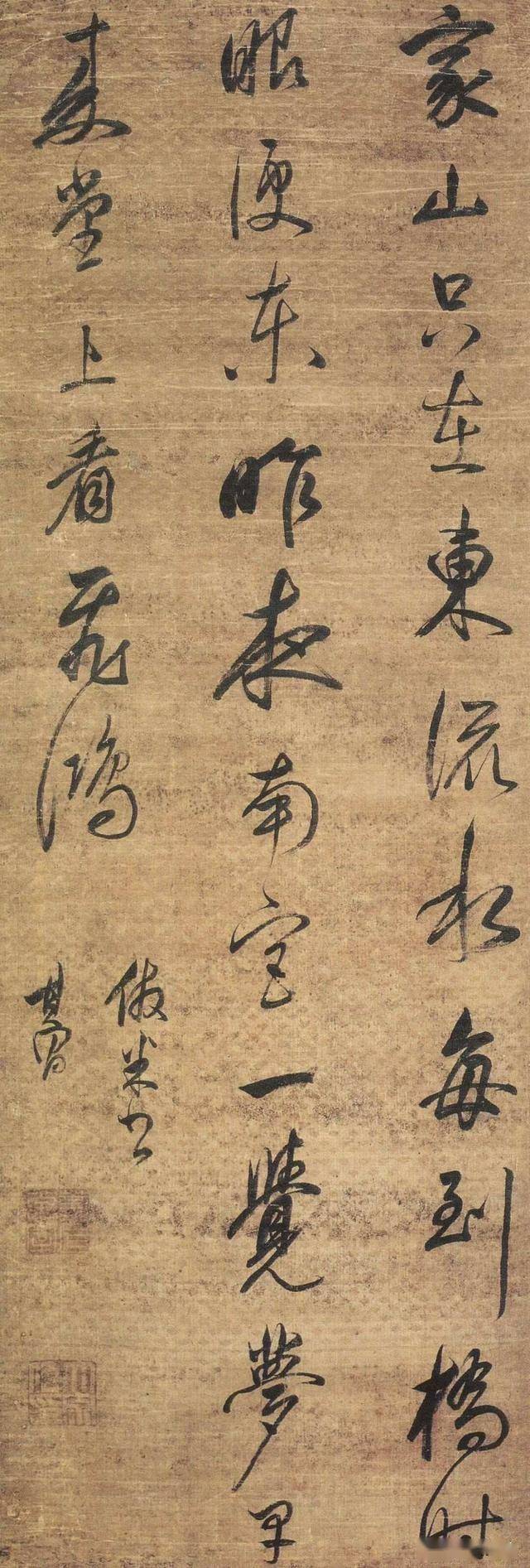
�ߡ�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�w��е���Փ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w���\�ġ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u(p��ng)Փ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һ�l�����ġ�ġ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w���\�顰���ӡ����ڕ�Փ�wϵ���P���J(r��n)֪�c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S���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ϵ�y(t��ng)�Գ�Խ����K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ԡ��ؚw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ĵĂ�(g��)�Ի���Փ�wϵ��
�@һ�^�̽�ʾ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y(t��ng)ˇ�g(sh��)ʷ��һ�N���͵ġ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Խ��ܡ��C(j��)�ƣ����˲��Ǻ�(ji��n)���^��ǰ�t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Ԍ�(du��)Ԓ���ڽ☋(g��u)���ؘ�(g��u)���ڳ�Խ�д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ɹ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\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Ϸ�����vʷ��Ȼ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J���أ���ī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ң�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0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