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ˇ�g(sh��)�ӑB(t��i)] 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L(f��ng)�𡪡����w���c���Ĵ���Ԋ�˂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
��3 ���� 23 ����x 2025-09-16 20:15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L(f��ng)�𡪡����w���c���Ĵ���Ԋ�˂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
���ߣ�ˮ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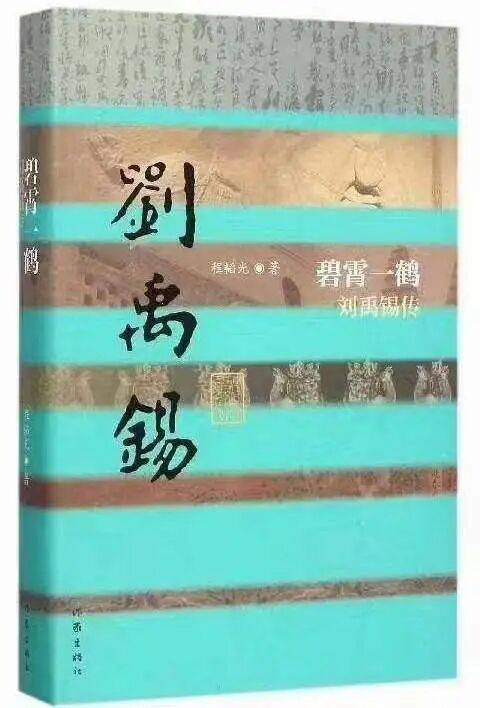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
һ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ƽ�ġ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Ҫ�˵���ƽ�˷�(w��n)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͕���ˮ���ˣ��@����ƽ�t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ӄ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ô����г��˵�ħ�����o��֮�����ѿ�һ����
Ԋ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ƪ�vʷС�f���ҳ��w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Ԋ�~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p�塣�������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˰��ﶴͥ��һ�ӡ���h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ƺƜ������M�o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ꎣ������f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ԊՓ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Ǻ�ţ�䗝������ö�e��
�r��ǧ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݅����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ܻ��ĝL�L�t�m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֮ҕҰ���۹���đ�R����Խ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`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Ƴ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̫����յô��һƬ���S���@���ի@�ļ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Ҳ�DŽڄ��߿�g�Ĺ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҅s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ƴ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ꖹ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i�c���·����ʢ�Ƶ����~���ÿһ�η����� Ҋ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vʷ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ľ����Ĵ���Ԋ�˂�ӛ���ڹ╞��չ�_����F�R�Ļ�����Ą���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һ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֮�|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Qֱ�ϱ�����
�@λ������ԭ�ϲ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F(xi��n)���P����Ԋ�˂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(sh��)�˳������֙C��Ƭ����x�r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)�ֵ����Lƪ�vʷ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᯼ŵĹŴ��ČW(xu��)ʷ��ጷ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L�[���@���Ǻ��εĚvʷ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Խǧ��ľ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Ҋʢ�Ƶ�܇�R�c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I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žž�����
Ԋ��һ݅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ώ��״�Ԋ������һ݅��Ҫ�Ў�ƪ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ϵ۵�ҕ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ء��n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˼���vʷ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挦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ӹ�Đ���Ҳ���У�
�u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
�w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dz����ϵ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ܐ�ڡ��丸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ĸ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;�У���֜��˾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;��뽡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ȡ�
����׃?y��u)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h�ݵ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ˣ����г��L(f��ng)�z������Εr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պ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֪�ݣ�һ�ɴ��֮�����
�w�����ꌑԊ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Ƴ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Ƴ���ͬ�r���Ă��д����ԵĴ�Ԋ����ס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IJ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턦����Ԋʥ�Ÿ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�����˚vʷС�f�����Դˌ��Ƴ�Ԋ�˺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С��̽���ᳱ���w��Ҳ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Ԋ���Ƴ�Ԋ�˵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У�ĉ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v�n�װو����۽z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f���Ķ��ɞ���x��Ԋ�ʹ�Ԋ�˳��L�^�̵ġ���(d��o)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Ԋ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ˡ���ͬ�rҲ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ˆT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ؔ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Ľ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A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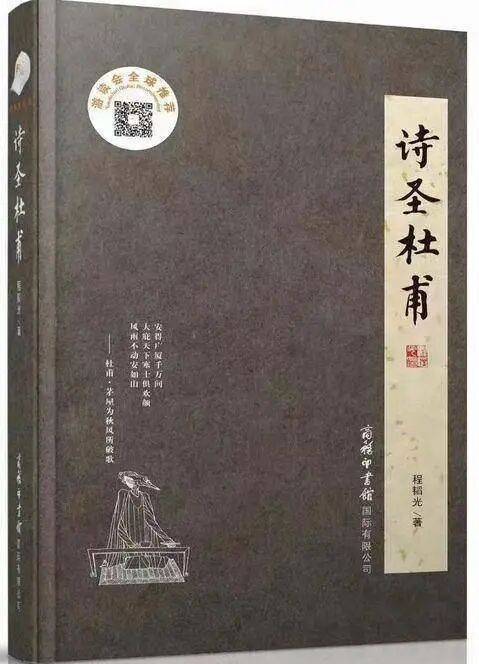
��Ԋʥ�Ÿ���
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¡��L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һƥ�ĝh�ƹŵ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R���y����ԭ���صij��L(f��ng)�h퍣�ߵ푮�(d��ng)���ĉ��ij��T���@λ��Ԋ�ԹP�|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ס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Lƪ�vʷС�f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䓽�ɭ������ʧ�r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ƽ�ƞ齛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ݹųlj��µ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a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w��վ�����zַ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dz��ˡ��`·�{�|���Ԇ�ɽ�֡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I(y��)ʷ���h̎�Ƿ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ݕr���µĻ��ޕ�Ժ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ɷN�Ļ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Ѫ�}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c����đn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ڡ�̫���턦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M�Ŀ�ݣ��ڡ�Ԋʥ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D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ݕr�ġ���֦�~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[��һ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ġ�ͨ�`���xʽ����ʷ���õĠT���c�佭�O�����xӳ����ʷ�c�O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Խ�A�ӵ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D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ӵĕ�ӛ������С�f�ҵ��@�R�^���ƴ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ĵ��O�y��
�@�N�p��ҕ����ںϣ����ĚvʷС�f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صărֵȡ�����ڡ��L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H�Ƿ�̖|����Ҋ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⽨���֪�R���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翼�ŌW(xu��)�Ұ�x���vʷ�ĵ،ӣ�����ǡ��ȶ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̎�����Mʿ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đn̿�vԸ�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ڸ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挦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
�ڡ�̫���턦���У����☋(g��u)�ˡ�Ԋ�ɡ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ڽK��ɽ�����tǰ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ݡ��r�����w��ע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џ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й¶�����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潹�]�����ڡ�Ԋʥ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ԭ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ҕ�X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Fլۡ�A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cؚ��ߵ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L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е�Ѫɫ�ۜI��
�w��ܽ^ƽӹ֮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֪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֪�R���ӑ�(y��ng)ԓ��֪�R���ӵē�(d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҂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Щ�@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߮�(d��ng)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Ҋ��đ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Ҳ؞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ʼ�K�����P�µĶŸ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͟o�ε�ԩ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ČW(xu��)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ć�(y��n)�C�ԣ�ǡ�Ǯ�(d��ng)���ĉ����F��Ʒ�|(zh��)��
Ԋ�˶Ÿ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ǎ���Ѫ�Ŀ��V���w�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r���O(sh��)Ӌ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֪�ĈD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˱�횳����Z�ԵĽY(ji��)ʯ֮ʹ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r�Ռ�Ԓ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֪��Ҋ�C���y�r�IJ��ɳ��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ǡ�Ԋ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І�ľ������ԁ֮�أ��dz��ˡ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ǻ��ޕ�Ժ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n���n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ĹP�h����Ȼ�y�����@��ˮ���ķ�̖�ܴa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_���c����đn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ͬˮī���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ײ���@�˵ď�����
�ڡ�̫���턦���_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Ɖ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ԭ�ġ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ɂ����ؿ��˸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儦�c��Ľ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xӳ���¹��³��o�ľŸ蹝(ji��)���c��Ԋ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Խ�r�յČ�Ԓ��ǡ�����ݹųlj��ϰ��g�ĺ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c��ԭ�Ĝ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ڳ��w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ɪ��ص��Ļ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P�|�D(zhu��n)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ڡ�Ԋʥ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ʥ�Ÿ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оo�oé�ݵ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͡��ӏR��֮�߄t�n���ļ�Ӱ�دB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ڴ˽�ʾ��һ���@�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ʢ��Ԋ�˵ľ���D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н�ǧ�d�đn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Ҳͬ���þ�һ�ӡ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r�g�Ľѳ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r�Ěvʷ���f��Ҳ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ū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Ŀ�܃�(n��i)�v���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Űl(f��)�@�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˿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ͻȻ�D���w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ľ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ġ�̫���턦���Ă��Խ�ŵ���Ԋʥ�Ÿ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(d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ġ��L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쵽������һ�Q���ij�Ȼ���_��ǡ�Ƅ����a�P����ֻ��Խ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ښvʷ�ı����τ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IJʺ����ҽ�ʹ�ļ��˿�Ҳ�·��L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Ҳ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ā����ǒ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衪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҂��o����׃?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ij�_����f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֮ˮ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|ȥ�˻�ӿ���w����Lƪ�vʷ�����ӛ��Ҳ�͕��е�Ԋ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ǹ�o����
[���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҅f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ϯ���ؕ��L]
(����ԭ�d�ڡ���ԭ�ČW(xu��)��2025��8�¿�)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2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