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ږ|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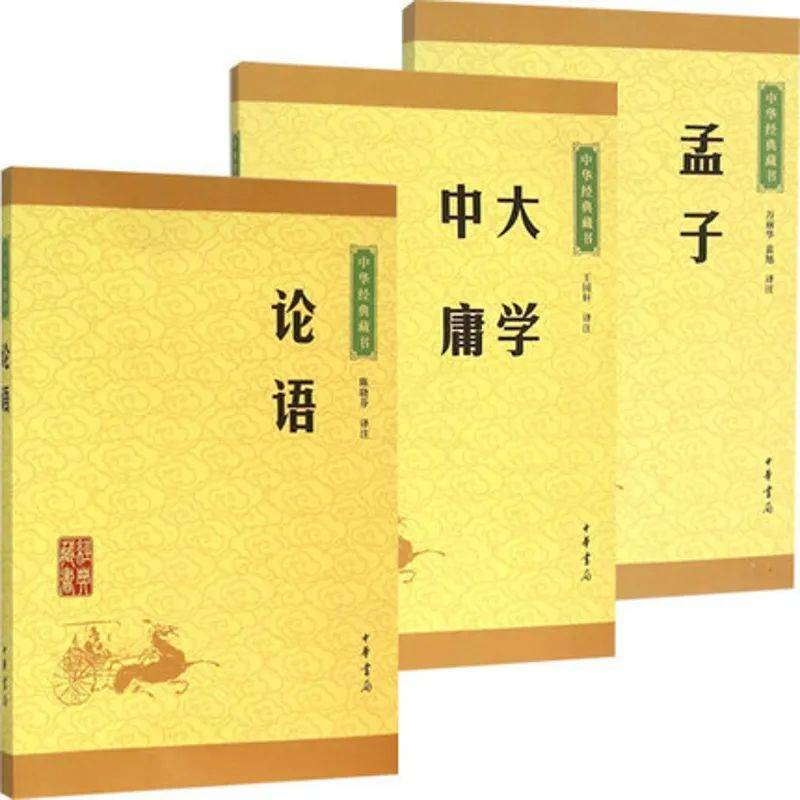
�ڽ���֮ǰ�Ė|���^(q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ձ���Խ�ϵȇ��Ⱥ�ϵ�y(t��ng)�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W(xu��)˼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ĵġ��Ļ���ͬ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ɫ��һ�ȳɞ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Խ�����ߵı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Խ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ע�⡱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鲻��֮Փ���c֮�෴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ĽӼ{�s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☋(g��u)�ȶ�Ԫȡ�����γ��˪�(d��)�صġ��ĕ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ږ|������Ȧҕ���¿��조�ĕ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׃�w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γ�
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W(xu��)ʷ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^��ʼ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ġ����y(t��ng)Փ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^֮�����ܶ��U�ġ�̫�O�D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ġ�̫̓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ı��¡��W(xu��)ӹ������Փ�ϲ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ڴ�֮ǰ���M�ɡ��ĕ����ġ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ĵ�λ���ͬ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Yӛ���г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Փ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ϷQ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@�c�ƴ����ڷ�̌���W(xu��)�ě_�������ߵĻ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
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̲������ƴ�˼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(j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̎��һ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Vϵ�����̾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ڡ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W(xu��)��ȱ�ݡ��n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Vϵ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ˡ����y(t��ng)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ϵ���ɴ˴��M(j��n)�˿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͡����ӡ��IJ��Q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̵ġ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ᳫ���˽Կɳɷ𣬾��ИO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硶���ӡ����Yӛ�еġ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δ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P(gu��n)ע��δ�ġ����ԡ�ҕ���M(j��n)�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ԕ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Գ�ʥ���ķ���Փ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ġ��ķ�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Ϳɳɞ顰ʥ�ˡ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ͷ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˽Կɳɷ𡱵ĽK�OĿ��(bi��o)�߶�һ�£������ٟo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ĵ�λ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Ҫ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伮��
�^֮���ܶ��U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f�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ԏ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̫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ѡ��ԡ��֞顰����֮�ԡ��c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֮�ԡ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ԡ����Ǐġ����|(zh��)֮�ԡ���(f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֮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^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Ľ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顰����֮�z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ġ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ԭ�ļ�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ġ����V�I(l��ng)���͡��˗lĿ�����Ǻ��εĵ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˵ġ����R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ӑ�����f��ı��w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W(xu��)�ĵ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ּ?x��)w���c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̵��˸��M(j��n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Q���͡���Փ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һ�w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�Z�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U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ԡ����F���M�ԡ�����ӹ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ڏ��d�����̵Ļ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ҕ��?q��)���Փ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չ�_�µ�ԏጣ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ϷQ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182�굽1199���g��ο��̡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γ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ڕr�ڣ�1224��1264�꣩���ܶ��U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̼����䱻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δ�@ȡ�ٌW(xu��)�ĵ�λ��ֱ��Ԫ�����ڕr�ڣ�1311��1320�꣩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ɞ���e��ԇ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춨����ٌW(xu��)���ݡ�
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߳ɹ��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~�ԁ���̌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c�_����ʹ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Փ�Ķ�̎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얹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߀���S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Խ�ϡ��ձ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_��(chu��ng)�˄e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W(xu��)��
���ĕ����ڳ��r�cԽ�ϵ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s��13���o(j��)ĩ���ɸ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߰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س��r���_���ˡ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ڳ��r�Ă���֮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ڷ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˲��Լ��ų��̵ȷ���l(f��)�]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18��1392�꣩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Ӟ�ɾ��^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C(j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Ľ̌W(xu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ϳ��r��1392��1910�꣩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ԇ�ġ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ڳ��r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ɞ鳯�r�˱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ɞ����ϳ��r��ٶ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
�ڴ����g���Ⱥ�ӿ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꣨����Ϫ�����ɜ�����ţ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壬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Q�鳯�r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ăɴ�߷塣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I(l��ng)���՝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ԭ���f���f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t�Č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P(gu��n)ϵ�ǡ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S֮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䑪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˵ġ����顱�P(gu��n)ϵ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еġ��Ķˣ����x�Y�ǣ�֮�ġ��顰����֮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ʼ��ƶ��o�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֮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ϲŭ�����ې������t�顰�⡱֮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Ľ��x��(y��ng)��(c��)�ء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˵ĵ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c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֮�g���P(gu��n)(li��n)���c֮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顰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⡱���o�Ⱥ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P(gu��n)ϵ�顰�����t�ӣ����o��t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ˡ��Ľ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ʡ��Ķ�֮�ġ������顱�Ԟ顰�⡱֮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ƣ���֮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}�j(l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Ľ��x��횡��⡱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ʹ���⡱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̣��˞顰�ĕ����ĺ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
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oՓ�ǡ������ɡ�߀�ǡ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ߵġ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δÓ�x��Խ�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�ֻ�ǽ��x�Ă�(c��)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̎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֮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x���Ƿ��ϡ��ĕ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l(f��)�ˡ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⡱֮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һ���̶����Ƅ��ˡ��ĕ����ڳ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춨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λ��
�c���r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13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Խ��ꐳ���1225��1400�֮꣩���õ��ٷ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Џ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賯��1428��1789�꣩�����ٷ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߀���ƿ��e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鿼ԇ����Ҫ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춨�ˡ��ĕ����Ĺ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ʹԽ�ϵ��x���˶��ܡ��ĕ�����Ӱ푶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ʿ�B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r���߲�ͬ���ǣ�Խ�����ߎ���ֱ���^���ˡ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֮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Č�(sh��)�W(xu��)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˰ѡ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ĕ��s�⡷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(j��ng)�䡣�^֮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nj�(sh��)�п��eȡʿ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ı��x֮����
�@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ߺ�Խ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ע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Ծ�����ʹ�dz��r���ߵġ���⡱֮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Խ��W(xu��)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r��Խ�ϵġ��ĕ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Ї����ĕ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ķ����c���u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沢�o̫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Ҋ��
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׃�w
���ձ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ĕr�g����13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ɮ�H֮�g���@һ��rֱ��17���o(j��)�Ľ����r���Űl(f��)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ڵ´��ҿ�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̽y(t��ng)�Ρ������ǵ´��ҿ��x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S�o(h��)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֧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ӌW(xu��)���_ʼ���ձ�ʢ�У��Ⱥ�ӿ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ӌW(xu��)�ɣ���ԭ�ʸC�����_ɽ�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ӌW(xu��)�ɣ����|ʡ����ؐ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ӌW(xu��)�ɣ����Еr��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@�˽������ӌW(xu��)�ď�(qi��ng)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Ҫ�P(gu��n)(li��n)�ġ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S֮�������ɞ齭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ɽ����ı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ͬ�W(xu��)�ɵČW(xu��)�߂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Ӱ푶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s�l(f��)���˹ŌW(xu��)�ɽ☋(g��u)���ĕ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¼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Ќ�(sh��)�ٺ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cݶ���ޏƞ�ŌW(xu��)�ɵ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(f��)�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U����ע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⡰�ĕ������Ⱥ�☋(g��u)�ˡ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ҕ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ŌW(xu��)˼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͡����ӡ��t�ǡ��˂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w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ǿ���֮�z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(ji��)�顶Փ�Z��֮���x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롶��W(xu��)��֮�еġ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֮�f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x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ı�ּ�����ҏġ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ԭ�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鿴�صġ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Ƚ�δҊ�ڡ��Z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ֻ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ԏ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顶��ӹ���顶Փ�Z���ġ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ˡ��W(xu��)ӹ���ڡ��ĕ����е���Ҫ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ֱ��׃?y��u)顰�Z�ϡ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ġ���Փ����ͬ��ݶ���ޏƵġ���Փ����Ҫ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ַQ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ܷQ�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Ј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m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�ڌW(xu��)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ӿɷQ�顰ʥ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ٟo��ʥ�ˡ����ǹ���ݶ���ޏ��ԡ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☋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ġ����ϲ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Ӳ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е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Ҳ�y���c��Փ�Z���ȼ硣���ڡ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͡���ӹ����ݶ���ޏ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Ľ��x�Դ��и����Ե��e�`�����x�ˡ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ԭּ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ȫ��ݶ���ޏƏص☋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ֻʣ�¡�Փ�Z��һ���ܷQ�齛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Q��
�@Ȼ���c����ġ��ĕ��¾伯ע���Լ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ߵġ��ĕ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ȣ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^ֱָ���嘋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_ʼ��ݶ���ޏƵ���ͨ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еġ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Ľy(t��ng)���顱�Ȍ����˂�֮�����]��̫��Ҫ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嘋(g��u)���ġ����w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x�˻����ġ��˂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Ԃ�(c��)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ġ��˂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ġ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ɫ��
�Ė|��ҕ�조�ĕ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Լ�׃�w�^�����o�ɿ��Ԕ[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džΪ�(d��)�ؿ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Խ�����ձ��ġ�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ȵ��۹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ġ��ĕ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ȿ϶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Խ�ϡ��ձ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ʹ�@һ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ӽ��|�����ĕ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Դ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ƌW(xu��)��2023��11��8�յ�6��
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vʷ�W(xu��)Ժ������Ժ�L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1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