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G�裺�ČW(xu��)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ǷN��ʽ߀�Ǜ]��׃

�G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6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С�f��֮һ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á��� �x ���Ї�С�f50���� 1978 �� 200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ƪС�f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Ї�С�f100����1978��202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⣬�ಿ��Ʒ���ľ��Ĕz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H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Є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ȶಿ�ك��LƪС�f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Θs�Ǹ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ꐲ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ͯ�ČW(xu��)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ݡ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��ȵ��e�k���˕���չ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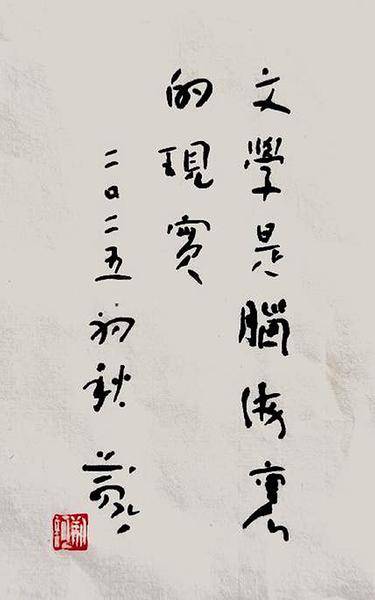
�G��o��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x�ߵ��}�~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ӛ�Ä��_ʼ��С�f�r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s־�϶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^ȥ���Ї���õ��ČW(xu��)�s־�ġ��ի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ʮ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͡��F(xi��n)�ڣ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Ʒ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s־���ں��s־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һ���s־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ɶ��ͬ��
�G�裺�Һ���Ҳ�]�f�^�@�ӵ�Ԓ�����_ʼ��С�f�ĕr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ݽ����С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ի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߀�б�ʡ�ġ��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ҽo���ի@���ĵ�һ����ƪС�f�ǡ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ij���ͽӵ��˳����´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fҪ���@��С�f��ֻ����Ҫ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@�o���ҘO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һ����ƪ��̫ƽ���Ľo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Ɍ��o�ҵ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ϲ�g�@��С�f���϶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҂����ɞ�����ѵġ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Ҿ͌�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nj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пվ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˺ܶࡣ�o�����ǡ��ă�ƪС�fҲ�ǼĽ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нo�Ҍ������Qٝ�ҵ�С�f���c�锵(sh��)����Ďׂ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dɫ�����ҽo���ɽ���ĵ���һ�M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R�Kͯ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@�M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ڡ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X�Ì��úõ���ȻҪ�o��һ�c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@�����ǰl(f��)���úܶ���һ���ж�ʮ�ׂ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LƪС�f���Ѓ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(n��i)�l(f��)���ġ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Ѹ�ČW(xu��)Ժ�ø��а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ի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ֽo�Ҵ���40����Ԓ��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ñ��^�࣬ͬһ�ҿ��ﲻ����ÿ�ڶ��l(f��)�ҵ�С�f����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ČW(xu��)�s־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댑��С�fҲ�������@һ·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Ȥ��ʲô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ܰ��ˎ���һ�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˲��ܫ@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һ�N�R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ĵ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ú��S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ǘ�ȤҲ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�e��ʹ���c�g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o횳����κν�ͨ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�����ҬF(xi��n)�ڴ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ϯ���҅s����һֱʲô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߀�ڌ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ħ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�ϰa�ľ����p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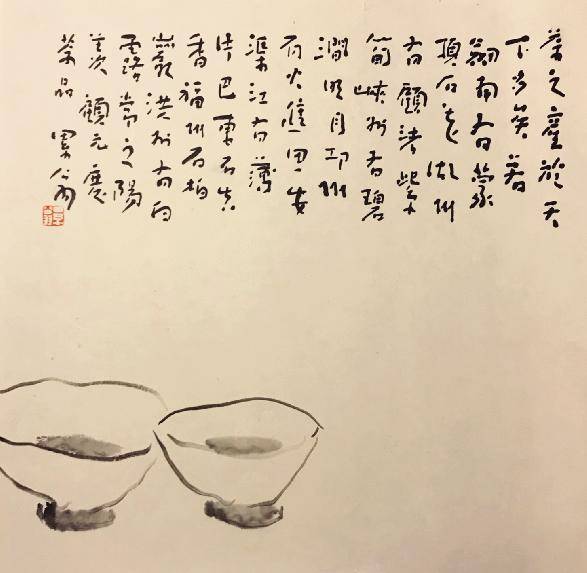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LƪС�f����ˎ���@�ÏV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L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G�裺Ҳ�]�Ы@�ÏV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ܱ��^���J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ā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䌍�Ǻ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K�O���x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x�҄���Ҳ�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һ���Lƪ���oՓ���}��߀����ɶ����Ҷ��X�ßo�����Լ��Ąڄ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֮����uҲ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Ҵ��Ԓ���f�x�����X�úܺá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uՓ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@��һ��Ԓ���f�G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гɾа����@���Lƪ�ڼ��g(sh��)�ϴ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ԕ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A�s��һЩ�uע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fԒ���Z�⣬�䵽�����ϵ��L���cɫ�ʿ϶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һ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;����ஔ?sh��)IJ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Ҫ�@�N��ӵ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߉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˺ܴ�Ĺ������y�ȵČ����Еr������y�ܹ����o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ľ����п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Ǖ��кܴ�Ę�Ȥ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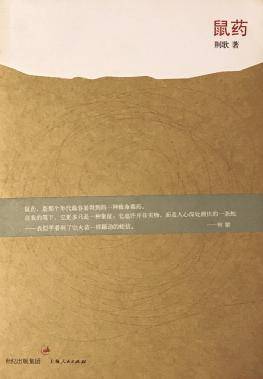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Ǻ�20���o90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�ģ����w�Ƿ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h�ČW(xu��)�ij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]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Ʒ�g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Ͳ���ȥ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нK�ؔ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С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(x��)�T����Щ��Ʒ�����Һ��@ϲ������ͻȻ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С�f��ʲô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С�f�ǿ����@���ǘӲ��Ҳ�ֻ���@���ǘ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ʽ���ӵ����Ҿ͇Lԇ�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f�����ǘO�䂀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X�Ì����ߎ�Ҳ���DZ�һ�ɕr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ߵ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֪���Ǐ�ʲô�r������Ϣ�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ֶ��ص����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ҵă�(n��i)��߀�Ǻܲ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Ҫ�f���ǣ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�hϴ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ڵČ�����߀�Ǖ�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ܲ�һ�ӵ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H����ʽ�ϵ�ð�U����Ҳ���b�ؓ�����ƽӹ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˺�_���S���Թ̵���(x��)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Ó�x����͵��µ�܉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һ���v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Dz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ཛ(j��ng)��Dz��ڹ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Ԓ�ķ�ʽ���ܲ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߀�Ǖ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�h�ČW(xu��)ϴ�Y�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ŕ�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䌍�^ȥ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Ʒ�P(gu��n)ע�c���ܶ���С��ƫ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ĵط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߲���̫����Ӱ�Ҳ�����ܴܺ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\ʹȻ��Ҳ�]��ʲô�ñ�Թ�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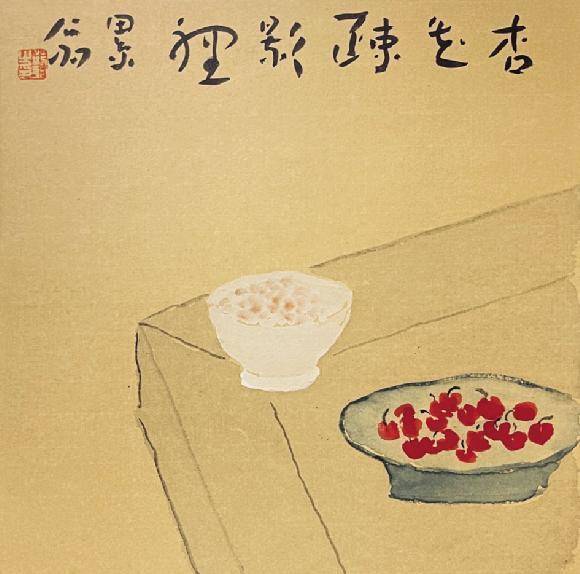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w���ڡ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G��ĕ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G��һ���IJŚ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ˡ�̫ƽ�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С�f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к�Ӱ푣�
�G�裺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˵�һ݅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¾͕����úܺ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@�N�dȤ���^�V�����˾Ϳ���ɶ���鶼������һ�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҄���Ҳ�f����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Dz�һ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ÿ�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ˌ���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Еr���X��һ݅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҂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˺ܶ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c�ղ������@һ�c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Ȥ����Ҳ�S�ĕr�g�;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Ӱ�һ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ǿ��Է��^���f�@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䌍����һЩͨ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һ��С�f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e�ӵ�ɫ�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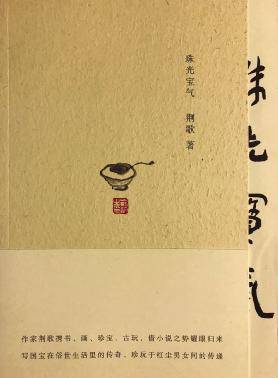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ƪ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Ҍ��˽���ʮ���С�f��һֱ���؏�(f��)һ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Ǿ��Ǽ�ͥ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߀�ڡ����ǡ��s־���^һƪ���L��ɢ�ġ����H��ĸ�ӌ�Ԓ������Ε�һֱ����ͥ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w�ij��L�;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һ���e���Ƶļ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@�ӵ�ԭ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ľ��Ǽ�ͥ�ɆT֮�g�ľo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Ը�Ҳ�����@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Ť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ĸ��H57�qȥ����ĸ�HҲֻ�66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ܿɑ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ĸ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̫��Ĵ����ĥ�y��Ҳ���ҵ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ôԹ�������Ǹ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̫���K��̫�ɑ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ڮ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£��Dz��H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Լ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һ����Ҳ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ĸ��H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Ό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Ӱ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в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κ��¶��Ȅe�ˏ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��θ�У�L�ͽ̌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̔�(sh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Ӣ�Z��Ӣ�Z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V���ԌW(xu��)�ġ���߀����һ�ֺ������ͮ�Ҳ���úá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ǂ��\���_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춼�Գ�����ˮϴ����ÿ��ȫУ�\�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ǂ��r�����еIJ��Һ�ʹ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�K�Vʯһ�ӣ��ڼ�ͥ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к����侀���҂��ҵĚ��ʼ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˶��]�п옷�����ܿ옷��ꎳ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ǂ��ҵij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@�ӵ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ȻҲ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˺�˼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Ը��@�ӵ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߁��fҲ�S����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Ҫ�@�ӟ��ɣ��Ҍ��ɲ�Ҫ�ɞ��@�ӵ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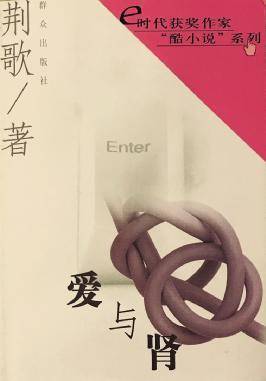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˺ܶ��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Ʒ���@����ꐲ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Ã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Lƪ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Ȼ�D(zhu��n)�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
�G�裺С�f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Ҳ�X���nj�����һЩͦ���e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˽�(j��ng)�ĵV���ƺ�Ҳ���c�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÷�״΄��ҿ��ԇLԇ���c�|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Ӛ�����һЩС����ϲ�g��Ȥζ���Ҿ͛Q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Qһ�N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ܽo�Լ����팑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һ�_ʼ�ĕr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߀��Щ��ֵ��뷨���X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ȥ���o���ӂ���x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υ���һ���P���ĕr����Ѓ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Ҍ����f���ゃ�������܈�҂��İ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һ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m�Ϻ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ֲ�ʧ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顣��ȻҲ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Є�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ȥ���@ʮ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˶�ʮ�ױ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һ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еĺ�ͯ��߀���кܴ���x���� 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ˌ��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ǰ��ղ��÷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Ԓ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ϲ�g �� �ö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̚������\�挍��̓�Σ����ֲ��ǜ\�����@�ӵĹ����Ǻ��y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õă�ͯ�ČW(xu��)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С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ӵĘ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ζ���@�Ӿ�̫�y�ˡ�Ҫ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Ҫ�ں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Ǿ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y�c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Ժõ��}�ġ��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M�X֭��Ű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̫ꖵ��]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Ąe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K�ݵ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˂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ؚ�F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ֻ���G���@�ӵ��˲��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˻�Ã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
�G�裺�Ҳ��]���X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Ȅe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ǐۺñ��^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DZ��^���Եě_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绨�X�IһЩ�Ŷ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mȻҲ���d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ٸ��T�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ٖ|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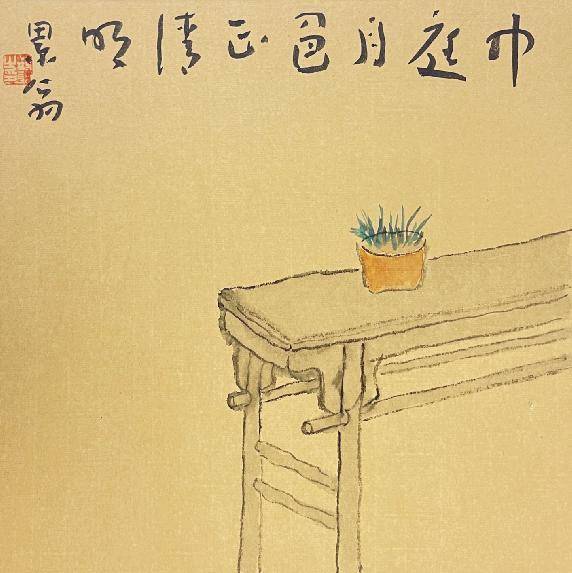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ܶ����f�G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҄�(w��)���˟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҄�(w��)�Ǻܻ��M�r�g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η��䌑�������҄�(w��)�ĕr�g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˵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ҵ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ʹȻ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ڼҕr�g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�N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в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Ҳ�ь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˞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Ǜ]�����x�ģ����@���ҿ옷�ػ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y(t��ng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ȁ�֮�t��֮���]����·���Ǿ��ßo��(sh��)��С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o�����أ�ÿ��ÿ�붼���ܴ��ȣ����ܰѕr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ڟo��֮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Ҳ����@�ӵģ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ֻҪ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ͺ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@�ӵ��f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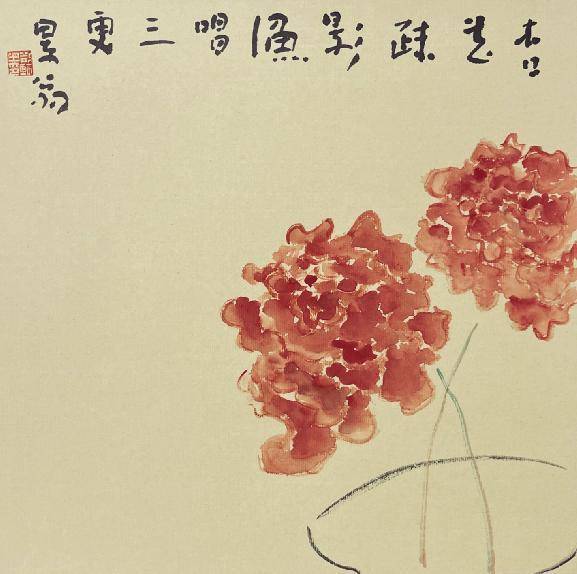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ˎ�ʮ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Л]������ƿ�i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Q�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��˿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ŵģ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Ҳ���Ɍ����ărֵ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ƺ���ijһ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˦Ҳ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u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lİ����·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ͨ�˺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į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ɽ��֮��Ļ�Ȼ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i���ܾ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Լ��^��ȥ���Ǖ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䌍��߀�Ǖ����Լ��ͽ���ԭՏ�Լ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ܲ����ͻ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Խ��Ҫ��Խ�Լ���Ҫ��Խ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Ǐص׆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Ҳ�ص�ʧȥ�ˌ����Ę�Ȥ��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ղأ�Ҳ���^�ܶ��@�����С�f��ϲ�g���桢�ղ���Ͷ�Y߀�Ǽ���ϲ�g��
�G�裺��ϲ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Ļ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ǿ�Ҋ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Ļ���ȫ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붼����һ���̶ȵ�ϲ�g���@Ҳ�Ǟ�ʲô�����ϵIJ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?n��i)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Ȼϲ�g������I�Ŷ��ղعŶ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£��^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ϲ�g���ﵫ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Iȥ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ȥȾ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|���L�U�ܴ����ٖ|��̫�࣬�����̵��_��̫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H��Ҫһ�c�e�X��Ҫ�Еr�g����ȥ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㿴��Щ�b����ҕ�l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Լ����ˎ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һ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µ���߀���߳�ŭ���@�f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J֪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Ę�ȤҲ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һ�ӣ��o�����e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͛]ʲô��˼����ȥ�δ��棬���а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ˇ֮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֮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И�Ȥ����Ԓ�f���R�Ų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vʷ�Ѓrֵ�ĺ����Ė|�����ǿ϶�����̝�X��Ҫ����Ķ��Ǽٖ|�����Ǿ��DZ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ˮ�Ȼ���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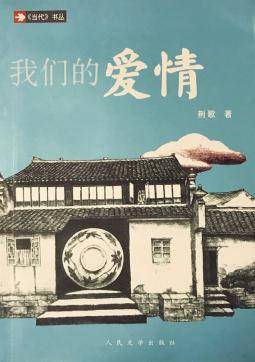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Ǐ�ʲô�r���_ʼ�ģ�߀ӛ�Ä��_ʼ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龰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ː��^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һ���ČW(xu��)СȦ�ӣ�
�G�裺20���o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hС�f���N���ɵ�Ԋ����Ȼ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˺ܶ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ɼξ��ġ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Ʒ�x��ϵ�Ѕ������ͷ·�ij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㣬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cԊ�裬����͌�ע�ڌ�С�f���]��Ȧ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С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Ц���¡����ǹ�܊�^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ĵ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Ͷ��ȥ�ĸ��Ӷ��ڸ��N��Ҫ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s־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·�߸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ܿ��^��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Ʒ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G�裺С�f���˛]��ƪ�Ͱ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ٱ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]�՛]ҹ�ز��·N�����ܿ�Ͱl(f��)ѿ���룬Ȼ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˼Zʳ����ֻ�ǼZʳ���Еr��ֱ���Ǒ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ԷN��Ȼ���֦�l(f��)ѿ�_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M�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ļ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ﶼ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ǂ��r���ČW(xu��)߀���й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Ӱ���
�G�裺�ČW(xu��)�o��?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ĺ�̎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ӹ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̓��(g��u)�c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�ﻨ�_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ij䌍�S���ò����ˡ���߀�o��?gu��)����˕r�g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�20���o90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^Ԋ������팑С�f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20���o90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]ʲô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e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ҿ϶��Ǻܻ��S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Ì�С�f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ϡ��ŹֵĹ��£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һ���g�v�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ͻ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m�p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С�f�_���o��?gu��)����˺ܴ�Ę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]�����x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ʲô�ӵ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Y(ji��)���˲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˘O����̵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�ҁ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ģ����ҟo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IJ�����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r�ڵ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
�G�裺�Ү���8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Z�Ľ̎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10�����@18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ҵ�С�f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ṩ�˟o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زĺ��`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ҵ�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c����ϲ�g�̕���Ҳ��Ը�����Ļ��^��Ⱥ���Ļ��o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ϲ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ɶ��ɶ�����ώ��ĕr���Ҿ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_ʼ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^��1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С�f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ǵ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f�Ҳ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̎����һ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Ǖr��1991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һ�_286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u�Ì����Ү��r�_���]�Д[��λ�ã���С�f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롣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Ҳ�]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V�Ԍ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˰a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]�k���Լ�ͣ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һ�ӣ��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ʎȥ���s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˻�һ�㡣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K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Ś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ʮ�ꌑ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ͳ�����1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1000�f���˰���
�G�裺�Ҵ_�����úܶ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1000�f�ֵ��Ǜ]�y(t��ng)Ӌ�^����Ӌ�]�а�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ā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ࡣֻҪ�M�댑���Ġ�B(t��i)���˾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ڲ��ڠ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cή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܌���Ҳһֱ�ڌ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ɢ�Č��ú����Еr���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ҵ�С�f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ɢ���Լ��X��Ҳ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ꌑ�˺ö�ɢ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ʮ�¡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ȴ��ϰl(f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顶���K�ݡ���ɢ�ļ������ɰٻ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ڡ����ҡ��s־���_�O(sh��)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䡱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Κv�鱳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S���Ė|����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ӵ�С�f���Ǻ�С�f��ʲô�ӵ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J�鮔һ�������ұȌ���һƪ��С�f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һ���õĮ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Ђ��˻�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ƽӹ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ʲô�܌���һƪ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Ԓ���@�Dz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Ʒ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ģ�ֻ�кî��Ҳ��ܮ����õĮ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Kͯ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Ŀ��ͲŴ�������ˮƽ��
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ݳ��˺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K�ݵ��Ļ����N���P(gu��n)߀�DŽe��ʲô���ɷ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K����
�G�裺ҪՓ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ݸ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Dz�һ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ؼ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^�l(f��)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K�ݵ����^�Ļ����N���S���r���䌍Ҳֻ��һ���f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ðɣ��҂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С�fɢ��Ԋ�裬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䌍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\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ڵ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cȫ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ЩԊ�~���x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ֱ�Ͳ���һ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Ҳ�ǣ��K�ݵ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ǺÖ|�����ǂ��y(t��ng)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б��l(f��)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Ҫ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o�Ğl�R��^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ɢ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α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c�K�ݵ��^ȥ�ǃɂ��wϵ����Ȼ�K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T���@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H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K�ݑ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и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Ļ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˼ҵĹ��E����ֻ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o�����B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ӡӛ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Ľ����ʹ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ǧ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ݽ���Ę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ȥ���K�ݣ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]��̫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ò�Ϸ·���Ҳ����ԭ���Ė|���ˣ��DZ����˲���֮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Կ՚�̓�ٵĸ��X���@�N���X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ÄeŤ���z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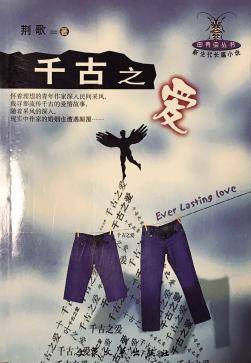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G����͏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͏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ģ�
�G�裺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R����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ܺã�����ؑ�(y��ng)��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߀���N�]�M���@�Һܸм���Ҳ�X�ÑM����

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Pӛ���ڡ��K���s־���B�d�����@�ú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ժ���͡�ɢ�ĺ���桷���^�D(zhu��n)�d������̖���ĵ��D(zhu��n)�l(f��)��Ҳ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ӛ������ˆҪ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ӵĕ���
�G�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ʂ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ǬF(xi��n)�ڳ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ļҳ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Ѓrֵ�ĕ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ărֵ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�c�ČW(xu��)ʷ�ăr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治�Hӛ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Ҳ��һЩ�Ļ��ϵ�˼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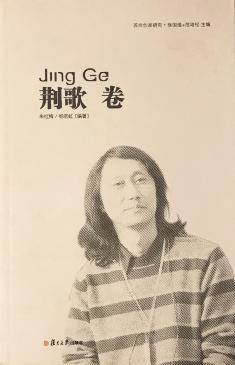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
�G�裺�䌍���ڌ�����ͬ�rһֱ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Ҳ�ĵ��ˡ��Еr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p�ĕr��]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Ҫ�Ǯ��r�D(zhu��n)ȥӢ�Zϵ����Ӣ�Z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ښW���Κ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Բ��С�Ӣ�Z߀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߱�ȫ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Ӣ�Z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ԌW(xu��)��һ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㏊���Ԍ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߀���̫�h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Z��̫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\�Dz��ܼ��O(sh��)�ģ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˻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һֱ�Զ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@�]�e���ܿ옷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
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ȫý�wӛ�� ���� �w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ڈDƬ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ṩ�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2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