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x�~߀���H�x�~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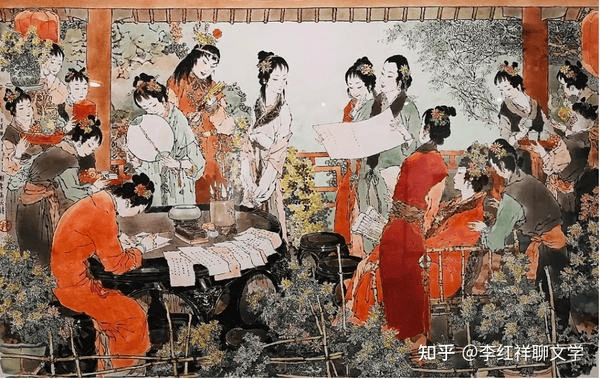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ӑՓ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Ć��}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}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Ҫ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桪��
�܌W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߲�ѩ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^�̵�һ���W�g�о��I��
֬�W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Z�Լ���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W�g�о��I����
�汾�W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̱�֮�g�Į�ͬ����׃�Pϵ���ղ�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W�g�о��I����
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Ժ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e�ڳ̸߱��鹝(ji��)�ġ�ԭ�鹝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ߡ�ԭ�⡱��һ���W�g�о��I����
���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ཻ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ɡ��t�lj�W�����Ȍ��T�о�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g�о��n�}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^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ʷ�Ƕ������^�ČW�Ƕ�ȥ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ķ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Ǐļ��ČW��ȥ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µ��о��I��Ҳ���Լ{�롰�t�W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ġ��t�W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F(xi��n)�@Щ�о��I���緭�g�����Ļ��о��ȵȡ�
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һ�N��W�ƵĴ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о����sɪ���m�˵���˼��Ү��˹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J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һ�N�о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о��t�W���Еr��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ı��_���]��ʲô�Pϵ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ܼҵ���ϵ�Pϵ�����T�о�һ�K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ٱ�Ů���˷�̔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^����혎�߀�漰���M�Z�Ć��}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ٹPīȥ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ַ���}���@���͡��t�lj���Ҳ�]���@����Ҋ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@Щ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о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Ƶ�߀�ЃȄո��ٌW�ƶ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xʷ�о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�r�¼{�롰�t�W�о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У���һЩ�x�߸��dȤ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ʲô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ӭ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ԭ����ͬ�ČO�B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ӵ��Ʉݲ����Z��ռ��(j��)���A��ֵĴ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ܼҵ��挍�vʷ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@Щ�ı��е��O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֮�����ƺ�߀�и�����V韵��[���ı���֧�Ρ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@Щ�[���ı�Ҳ�S�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@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ԭ��
���eһ���汾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汾�W�о����汾�Į�ͬ����Ҫ�Ǟ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õ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҇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İ汾�W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汾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ɗl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Ǖ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һ�l���x�߽��ܵ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ֺ��̘I(y��)ģʽ���P���x�߽�����r�ֺ͕r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P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ĸ��N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osplay���M���ˡ��t�W���о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@Щ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峯����ô�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Ԏ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˾��ǡ���ԭ����Ҷ�һ��ϲ�g�@�|������Ҍ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ⶼ��һ�ӵġ�
����ʮ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Ը�����ЙC���ĕr���桰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Ӌ�оł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⮔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͠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ٌ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^�ĸ��ܡ�Ҳ�S�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г��F(xi��n)�ĸ��N��Ƶġ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һ�ӵ��뷨��
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Ä��ֳɡ��܌W�������䌍��ѩ�ۼ�������ĕr����ʲô�|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·����@Щ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nj������⡶�t�lj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ڵġ��t�W����߀�nj����ČW�о��ķ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͏V韵ĵ�·���]��Ҫ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Ї��ŵ�С�f���P�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Բ��{�롰�t�W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Ї��ŵ��ČW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չ����
��Ӣ�r�Ͳ�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ČW�ģ�Ҳ�к���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к�˼��ʷ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r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ʷ�W�ҡ�˼�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Ա��Q�顰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ϡ���@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չ���^�Pע���Sһ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ۼ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Pϵ�Ŀ��CȥҊ�������ͺܸ��d�ؽӴ��˺ܾ���
�ǓQ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¾Ͳ������Sһ�r��ô�͟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Ҳ�����͏�����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鏈���̸���ǰ汾�W��̽���W���Ǽt�W��I(y��)�Ժ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ٶ༃�ČW�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@���I����Ҳ�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cƫ�ˣ��҂�߀�ǻص����ȁ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t�W���Ĺ����ҾͲ��؏��ˣ��Բ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�����ǿ϶����㡰�t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ڵ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顶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о�����ȻҲ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һ�T���W����ֻҪ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ʲô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㲻���f���f�Ͳ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Ƭ���ӵijɆT������鮔��Ҳ�ǟo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ֺÉ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@ƬС���ֵ����B(t��i)ϵ�y(t��ng)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ġ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С�Ԭ�܌W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Ҫ��Ԭö�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X�ø��@�T�W������Ҫ�ԷQ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Ҳ�]���}��
�ص��@���}Ŀ���ҿ��Ժ����fһ��ʲô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t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^���I(y��)�؏��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Qһ��˼·���fһ��ʲô�ˣ����÷Q����?y��u)顰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䌍Ҳ���^�P�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¼t�W�о������˾�ؕ�I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ڹŵ�С�f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G���t�lj��İ汾���}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˲��ٌ�ע����һ��]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Pע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쵽��ЦԒ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ղ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еĽ���ʷ����ϯ�ˡ��t�WՓ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}�v������һ�㲻�f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Ů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t�����l��(ji��)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úܲ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W�о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ˣ��P�ڡ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Îױ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֮�g�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ޱ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㡶�t�lj����汾����Bվ�����v�t�ǵ�ҕ�l�����Ǽt�W����
���ξ����㡶�t�lj����ɕ��о�����汾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Ǽt�W����
�Y�͚W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t�lj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˺�֮һ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Ŕ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ҵ��о��I�����ͼt�W�Ĵ��I���^����߀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Ď��T�����{ʲô�����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
���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䷶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W�Ƶġ��ҡ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f���H�x߀�ǰ��x��
Ҳ�S�@�����ҵČW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ĵͼ�ʧ�`���̶ȶ����˺ܶ������ԕ��X�á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�H�x�~��Ҳ�S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ġ��t�W���ČW�g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ܰ��б��µČW�ߺ�٩��ɽ�Č��ҷ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�׃���˰��x�~��
�����vʷ�Ͼ����@�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�ֻ����ЦԒ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Ԃ��fһ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ͨ�^�о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vʷ�Ľ����Pϵ������،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⡶�t�lj�����ҕҰ���˂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@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Ї��C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W�ҡ��ͳ��˰��x�~�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1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