’ď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ĆĎ“‚Ľ®ÝBģčÔL(f®•ng)łŮĶńÕ¨‘īģźŃų
’™“™£ļ
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◊ųěť20 ņľo(j®¨)÷–áÝ(gu®ģ)ĆĎ“‚Ľ®ÝBģčĶń÷ō“™īķĪŪ£¨‘ŕāųĹy(t®Įng)ŌÚ¨F(xi®§n)īķřD(zhu®£n)–ÕĶńÍP(gu®°n)śIēr(sh®™)∆ŕĺý◊ų≥ŲŃň≤ĽŅ…ļŲ“ēĶńňá–g(sh®ī)ōēęI(xi®§n)°£ĪMĻ‹∂Ģ»ňňá–g(sh®ī)…ķ—ńťL(zh®£ng)∆ŕőīę@≥š∑÷ÍP(gu®°n)◊Ę£¨»Ľ∆šĄď(chu®§ng)◊ųĆć(sh®™)Ř`…ÓŅŐůw¨F(xi®§n)Ńňēr(sh®™)īķ◊ÉłÔ÷–ģ输ƶ(du®¨)őń»ňģčāųĹy(t®Įng)Ķńņ^≥–ŇcłÔ–¬°£
Īĺőń“‘°įÕ¨‘īģźŃų°ĪěťņŪ’ďŅÚľ‹£¨ŌĶĹy(t®Įng)Ī»›^∂Ģ»ňĶńňá–g(sh®ī)Ķņ¬∑£ļ‘ŕĆŹ√ņ“‚»§…Ō£¨∂Ģ’ŖĹ‘≥–ņm(x®ī)őń»ňģč°įĻPńę „Ď—°Ę‘ä(sh®©)ēÝģč“Ľůw°ĪĶńĺę…ŮÉ»(n®®i)ļň£Ľ‘ŕőńĽĮŃĘąŲ(ch®£ng)…Ō£¨ĺýĪŁ≥÷°į÷–őų»ŕļŌ°Ęāų“∆ń°ĆĎ°ĪĶńť_∑Ň◊ňĎB(t®§i)°£»Ľ∂Ý£¨“ÚĶō”ÚőńĽĮ—¨»ĺ£®ĪĪ∑Ĺ–ŘúÜ vs. Ĺ≠ńŌ–„Ěô(r®īn)£©°Ęéü≥–√}Ĺj(lu®į)≤Óģź£®żRį◊ Į°Ę–žĪĮÝô vs. Ö«≤żīT°ĘŇňŐžČŘ£©ľįāÄ(g®®)ůw…ķ√ŁůwÚě(y®§n)≤ĽÕ¨£¨∆šňá–g(sh®ī)ÔL(f®•ng)łŮ≥ ¨F(xi®§n)≥ŲÔ@÷Ý∑÷“į°™°™ņÓŅŗ∂U“‘°į’żīůö‚Ōů°Īěť◊ŕ£¨ĻPńę–Ř◊ĺ…nĄŇ£¨÷ōö‚Ą›(sh®¨)ŇcĻ«Ń¶£ĽÖ«∆Ö÷ģĄt“‘°į«Ś—Ňž`–„°Ī“ä(ji®§n)ťL(zh®£ng)£¨ėč(g®įu)ąDĺę«…ž`Ą”(d®įng)£¨÷ōŪć÷¬Ňc«ťő∂°£ĪĺőńÕ®Ŗ^(gu®į)ąDŌŮ∑÷őŲŇcőńęI(xi®§n)Ľ•◊C£¨Ĺ“ ĺ∂Ģ’Ŗ‘ŕĆĎ“‚Ľ®ÝBģčįl(f®°)’ĻřD(zhu®£n)’ŘŁc(di®£n)…ŌĶń™ö(d®≤)ŐōÉr(ji®§)÷Ķ£¨’√Ô@20 ņľo(j®¨)÷–áÝ(gu®ģ)ģč∂ŗ‘™≤ĘŖM(j®¨n)Ķń—›ŖM(j®¨n)ŖČ›č°£
ÍP(gu®°n)śI‘~£ļ ņÓŅŗ∂U£ĽÖ«∆Ö÷ģ£ĽĆĎ“‚Ľ®ÝBģč£ĽÔL(f®•ng)łŮĪ»›^£Ľ÷–őų»ŕļŌ£Ľőń»ňģčāųĹy(t®Įn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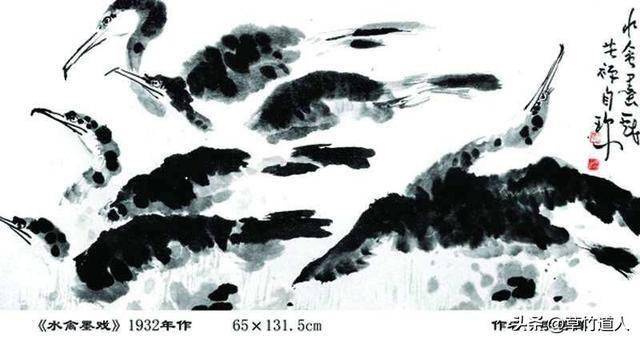
“Ľ°Ę“ż—‘£ļĪĽ’ŕĪőĶńŽp∑Ś°™°™÷ōĻņ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Ķńöv ∑ĶōőĽ
20 ņľo(j®¨)÷–áÝ(gu®ģ)√ņ–g(sh®ī) ∑ēÝĆĎťL(zh®£ng)∆ŕĺŘĹĻ”ŕ–žĪĮÝô°ĘżRį◊ Į°ĘŁSŔeļÁ°ĘŇňŐžČŘĶ»°įīůľ“°Ī–ÚŃ–£¨∂ÝņÓŅŗ∂U£®1899®C1983£©ŇcÖ«∆Ö÷ģ£®1900®C1977£©ŽmÕ¨ěťēr(sh®™)īķĺřĹ≥£¨Ös“Ú◊ų∆∑āų≤•”–Ōř°ĘĆW(xu®¶)–g(sh®ī)—–ĺŅúĢļůĶ»‘≠“Ú£¨∆šňá–g(sh®ī)≥…ĺÕ“Ľ∂»Őé”ŕ°įįŽŽ[°Ī†ÓĎB(t®§i)°£ĹŁńÍĀŪ(l®Ęi)£¨ŽS÷Ý√ņ–g(sh®ī)ū^ ’≤ōůwŌĶĶńÕÍ…∆ŇcĆW(xu®¶)–g(sh®ī)“ē“įĶńÕō’Ļ£¨∂Ģ»ň◊ųěťĆĎ“‚Ľ®ÝBģčÓI(l®ęng)”Ú≥–«įÜĘļůĶńÍP(gu®°n)śI»ňőÔ£¨÷ūĚuŖM(j®¨n)»Ž—–ĺŅ“ē“į°£
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…ķ”ŕŌŗĹŁńÍīķ£¨ĽÓ‹S”ŕÕ¨“Ľöv ∑’Z(y®≥)ĺ≥£¨Ļ≤Õ¨√śĆ¶(du®¨)őųĆW(xu®¶)Ė|Ěu°ĘőńĽĮľ§ éĶńēr(sh®™)īķ√ŁÓ}°£∂Ģ’ŖĹ‘≥Ų…ŪāųĹy(t®Įng)őń»ňľ“Õ•£¨‘ÁńÍĹ” ‹ĻŇĶšĹŐ”ż£¨ĺŖāš…ÓļŮĶń‘ä(sh®©)őń–řūB(y®£ng)£Ľňá–g(sh®ī)…Ōĺý“‘īůĆĎ“‚Ľ®ÝBěť÷ųĻ•∑ĹŌÚ£¨‘ŕņ^≥–Ö«≤żīT°Ę»ő≤ģńÍĶ»ÕŪ«Śļ£Ň…āųĹy(t®Įng)ĶńĽýĶA(ch®≥)…Ō£¨∑eėOŐĹňų÷–őų»ŕļŌ÷ģĶņ°£ňŻāÉĻ≤ŌŪŌŗň∆ĶńĆŹ√ņńłÓ}°™°™√∑Őm÷Ůĺ’°ĘķóķQň… Į°Ęļ…ŐŃ«›ÝB£¨Ĺ‘“‘ĻPńę „ĆĎ–ō÷–“›ö‚£¨—”ņm(x®ī)Ńňőń»ňģč°įÕ–őÔ—‘÷ĺ°ĪĶńĺę…ŮāųĹy(t®Įng)°£»Ľ∂Ý£¨»Ű…Ó»ŽŅľ≤ž∆š◊ų∆∑ÔL(f®•ng)łŮŇcňá–g(sh®ī)ņŪńÓ£¨ĄtŅ…įl(f®°)¨F(xi®§n)∂Ģ’Ŗ‘ŕ°įÕ¨‘ī°Ī÷ģŌ¬ŐN(y®īn)ļ¨÷Ý…ÓŅŐĶń°įģźŃų°ĪŐōŔ|(zh®¨)°£Īĺőń÷ľ‘ŕÕ®Ŗ^(gu®į)ŌĶĹy(t®Įng)Ī»›^£¨Ĺ“ ĺ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‘ŕĆĎ“‚Ľ®ÝBģč¨F(xi®§n)īķřD(zhu®£n)–Õ÷–Ķń≤ÓģźĽĮ¬∑ŹĹ£¨ŖM(j®¨n)∂ÝōSłĽĆ¶(du®¨)20 ņľo(j®¨)÷–áÝ(gu®ģ)ģč∂ŗ‘™…ķĎB(t®§i)ĶńņŪĹ‚°£

∂Ģ°ĘÕ¨‘ī£ļőń»ň«ťĎ—Ňc÷–őų»ŕļŌĶńĻ≤Õ®ĽýĶ◊
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Ķńňá–g(sh®ī)łýĽý£¨ ◊Ō»Ĺ®ŃĘ‘ŕƶ(du®¨)āųĹy(t®Įng)őń»ňģčĺę…ŮĶń…ÓŅŐ’J(r®®n)Õ¨÷ģ…Ō°£∂Ģ’ŖĹ‘Źä(qi®Ęng)’{(di®§o)°įēÝģčÕ¨‘ī°Ī£¨ĆĘēÝ∑®”√ĻP»ŕ»ŽņLģč£¨◊∑«ů°į“‘ēÝ»Žģč°ĪĶńĹū ĮŪćő∂°£ņÓŅŗ∂U‘ÝŃē(x®™)◊≠Ž`ĪĪĪģ£¨∆šĺÄól»Á°įő›¬©ļŘ°Ī°Ę°į’Ř‚OĻ…°Ī£¨úÜļŮńż÷ō£ĽÖ«∆Ö÷ģĺę—–––≤›£¨ĻPĺÄĄt»Á°įīļ–QÕ¬Ĺz°Ī£¨Ńųē≥ÕŮřD(zhu®£n)°£ĪMĻ‹ÔL(f®•ng)łŮŚńģź£¨Ķę∂Ģ’Ŗĺý“ēĻPńęěť–ń–‘Õ‚ĽĮ£¨’J(r®®n)ěť°įģč∆∑ľī»ň∆∑°Ī£¨ňá–g(sh®ī)Ąď(chu®§ng)◊ų «»ňłŮ–řūB(y®£ng)Ķń—”…ž°£Ŗ@∑NĆĘňá–g(sh®ī)Ňc»ň…ķļŌ“ĽĶńÉr(ji®§)÷Ķ»°ŌÚ£¨’ż «ňő‘™“‘ĀŪ(l®Ęi)őń»ňģčĶńļň–ńāųĹy(t®Įng)°£
‘ŕőńĽĮŃĘąŲ(ch®£ng)…Ō£¨∂Ģ»ňĺýĪŪ¨F(xi®§n)≥Ų°į÷–őų»ŕļŌ°ĪĶńť_∑ŇĎB(t®§i)∂»£¨∑īƶ(du®¨)ĻŐ≤Ĺ◊‘∑‚°£ņÓŅŗ∂U‘ÁńÍ ‹ĹŐ”ŕ–žĪĮÝô£¨ŌĶĹy(t®Įng)ĆW(xu®¶)Ńē(x®™)ňō√ŤŇcĹ‚∆ £¨÷ųŹą°įéü∑®‘žĽĮ°Ī£¨“‘ĆĎ…ķ≥C’żāųĹy(t®Įng)ń°ĻŇ÷ģĪ◊°£ňŻĻPŌ¬ĶńķóŲņ°ĘķėķÉ£¨ĹY(ji®¶)ėč(g®įu)ú (zh®≥n)ī_£¨Ą”(d®įng)ĎB(t®§i)…ķĄ”(d®įng)£¨√ųÔ@Ķ√“ś”ŕőųģč”^≤ž∑Ĺ∑®Ķń»ŕ»Ž°£Ö«∆Ö÷ģŽmőī÷ĪŔŔ ‹őų∑Ĺ√ņ–g(sh®ī)”Ė(x®īn)ĺö£¨Ķę‘ŕ…Ōļ£√ņĆ£«ůĆW(xu®¶)∆ŕťg£¨…Ó ‹ĄĘļ£ňŕ°ĘŇňŐžČŘĶ»»ň≥ęĆß(d®£o)Ķń°į»ŕļŌ÷–őų°ĪňľŌŽ”įŪĎ°£ňŻ÷ųŹą°į»°—ů»ň÷ģťL(zh®£ng)£¨—a(b®≥)ő“÷ģ∂Ő°Ī£¨‘ŕėč(g®įu)ąD…ŌĹŤŤbőųģčĶńŅ’ťgŐéņŪ£¨‘ŕ…ę≤ …ŌőŁ ’ňģ≤ ĶńÕł√ųł–£¨ ĻāųĹy(t®Įng)Ľ®ÝBģ賣ĺŖ“ē”X(ju®¶)ŹąŃ¶°£
īňÕ‚£¨∂Ģ»ňĹ‘÷ō“ē°įāų“∆ń°ĆĎ°Ī◊ųěťĆW(xu®¶)Ńē(x®™) ÷∂ő°£ņÓŅŗ∂UŇRń°įňīů°Ę ĮĚż°ĘÖ«≤żīT£¨Ķ√∆š…ŮňŤ∂Ý≤Ľĺ––őň∆£ĽÖ«∆Ö÷ģĄt∑īŹÕ(f®ī)—–Ńē(x®™)«ŗŐŔ°Ęį◊ÍĖ(y®Ęng)°ĘůĺŹ]÷ģ◊ų£¨”»Ķ√Ö«≤żīTĻP“‚°£ňŻāÉĺý“‘āųĹy(t®Įng)ěťłýĽý£¨Õ®Ŗ^(gu®į)°įń°ĆĎ°ĪĆć(sh®™)¨F(xi®§n)°įĄď(chu®§ng)‘ž°Ī£¨∂Ý∑«ļÜ(ji®£n)ÜőŹÕ(f®ī)÷∆°£Ŗ@∑N°įĹŤĻŇť_ĹŮ°ĪĶńĄď(chu®§ng)◊ų¬∑ŹĹ£¨ůw¨F(xi®§n)Ńň20 ņľo(j®¨)ģčľ“‘ŕőńĽĮŇŲ◊≤÷–÷ōĹ®÷ųůw–‘Ķń◊‘”X(ju®¶)ҨѶ°£

»ż°ĘģźŃų÷ģ“Ľ£ļĶō”ÚőńĽĮŇcĆŹ√ņö‚Ŕ|(zh®¨)Ķń∑÷“į
ĪMĻ‹Ļ≤ŌŪŌŗň∆ĶńőńĽĮĽý“Ú£¨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Ķńňá–g(sh®ī)ö‚Ŕ|(zh®¨)Ös“ÚĶō”ÚőńĽĮĶń…ÓŅŐň‹‘ž∂Ý≥ ¨F(xi®§n)űr√ųƶ(du®¨)Ī»°£ņÓŅŗ∂Uěť…ĹĖ|łŖŐ∆»ň£¨żRŰĒīůĶōļŮ÷ōĶń»Śľ“őńĽĮŇcŔ|(zh®¨)ė„Ķń√Ůťgňá–g(sh®ī)£¨Ŕx”Ť∆šňá–g(sh®ī)“‘°į–Ř°Ę◊ĺ°Ę’ż°Ęīů°ĪĶńĪĪ∑Ĺö‚Ŕ|(zh®¨)°£∆šģčÔL(f®•ng)»ÁŐ©…Ĺį„≥Ń∑Ä(w®ßn)–ŘŹä(qi®Ęng)£¨ĻPńę»ÁŁSļ”į„Īľ∑ŇļņŖ~°£ňŻ≥£“‘ĺř∑ýŃĘ›S◊ųģč£¨ėč(g®įu)ąDÔĖĚM£¨ö‚Ą›(sh®¨)Ī∆»ň£¨◊∑«ů°į’żīůĻ‚√ų°ĪĶń√ņĆW(xu®¶)ĺ≥ĹÁ°£ķó°Ęň…°Ę ĮĶ»Ó}≤ń‘ŕ∆šĻPŌ¬Ĺ‘ĺŖ”Ę–Řö‚łŇ£¨Ōů’ųĄā“„≤Ľ«ŁĶń»ňłŮņŪŌŽ°£
Ōŗ›^÷ģŌ¬£¨Ö«∆Ö÷ģěť’„Ĺ≠∆÷Ĺ≠»ň£¨Ĺ≠ńŌňģŗl(xi®°ng)Ķńž`–„ÔL(f®•ng)Ļ‚Ňc…ÓļŮĶńőńĽĮ∑eĶŪ£¨ Ļ∆šňá–g(sh®ī)ĹĢĚô(r®īn)÷Ý°į«Ś°Ę—Ň°Ę–„°Ę“›°ĪĶńńŌ∑ĹŪćő∂°£∆šģčÔL(f®•ng)»ÁőųļĢį„úōĚô(r®īn)ļ¨–Ó£¨ĻPńę»ÁĹzĺIį„ľö(x®¨)ńĀŃųē≥°£ňŻ∆ęļ√–°∆∑É‘(c®®)Ūď(y®®)£¨ėč(g®įu)ąD Ťņ ”–÷¬£¨÷vĺŅ°į”č(j®¨)į◊ģĒ(d®°ng)ļŕ°Ī£¨…∆”ŕ“‘ļÜ(ji®£n)ŮS∑Ī°£√∑°ĘŐm°Ę÷Ů°Ęĺ’Ķ»Ó}≤ń‘ŕ∆šĻPŌ¬łŁÔ@őń»ňÔL(f®•ng)Ļ«£¨≥šĚMēÝĺŪö‚ŌĘŇc…ķĽÓ«ť»§°£ňŻ‘Ý—‘£ļ°į◊ųģčŔF”–ēÝĺŪö‚£¨üo(w®≤)ēÝĺŪö‚Ątň◊°£°ĪŖ@∑Nƶ(du®¨)°į—Ň“›°Ī∆∑łŮĶń◊∑«ů£¨’ż «Ĺ≠ńŌőń»ňģčāųĹy(t®Įng)Ķń—”ņm(x®ī)°£
Ķō”Ú≤Óģź≤ĽÉHůw¨F(xi®§n)‘ŕ’Żůwö‚Ŕ|(zh®¨)…Ō£¨“≤∑ī”≥‘ŕĺŖůwľľ∑®÷–°£ņÓŅŗ∂U”√ńę°į…nĚô(r®īn)ŌŗĚķ(j®¨)°Ī£¨…∆”√Ěäńę°Ę∆∆ńę£¨ńę…ęĚ‚÷ōļ®ē≥£¨Ć”īőōSłĽ£ĽÖ«∆Ö÷ģĄt°į«ŚĚô(r®īn)√ųÉŰ°Ī£¨ńę…ę«ŚÕł£¨≥£“‘Ķ≠ńęš÷»ĺ£¨†I(y®™ng)‘žŅ’ž`“‚ĺ≥°£ņÓŅŗ∂U‘O(sh®®)…ęīůńĎ£¨Ō≤”√÷ž…į°Ę Į«ŗĶ»Ě‚Ń“…ę≤ £¨‘ŲŹä(qi®Ęng)“ē”X(ju®¶)õ_ďŰ£ĽÖ«∆Ö÷ģ”√…ę—Ň÷¬£¨∂ŗ ©“‘Ľ®«ŗ°ĘŰų ĮĶ»»ŠļÕ…ę’{(di®§o)£¨◊∑«ůļÕ÷CĹy(t®Įng)“Ľ°£

ňń°ĘģźŃų÷ģ∂Ģ£ļéü≥–√}Ĺj(lu®į)Ňcňá–g(sh®ī)ÔL(f®•ng)łŮĶń∑÷ĽĮ
éü≥–ÍP(gu®°n)ŌĶ «ň‹‘žģčľ“ÔL(f®•ng)łŮĶńŃŪ“ĽÍP(gu®°n)śI“Úňō°£ņÓŅŗ∂UĶńňá–g(sh®ī)◊VŌĶ«ŚőķŅ…Īś£ļ‘ÁńÍ ‹–žĪĮÝô”įŪĎ£¨Ķž∂®ĆĎĆć(sh®™)ĽýĶA(ch®≥)£Ľļůį›żRį◊ Įěťéü£¨Ķ√īůĆĎ“‚’ś?zh®®n)ų°£Ŗ@“ĽŽp÷ōéü≥– Ļ∆šňá–g(sh®ī)ľśĺŖ°į–őú (zh®≥n)°ĪŇc°į“‚◊„°ĪĶńŐōŁc(di®£n)°£ňŻľ»ņ^≥–ŃňżRį◊ Į°į√Ó‘ŕň∆Ňc≤Ľň∆÷ģťg°ĪĶńĆĎ“‚”^£¨”÷»ŕ»ŽŃň–žĪĮÝô°įĪMĺęőĘ£¨÷¬ŹVīů°ĪĶń‘ž–Õ“‚◊R(sh®™)°£∆šīķĪŪ◊ų°∂ Ęļ…ąD°∑°∂Ű~ķóąD°∑Ķ»£¨őÔŌůĹY(ji®¶)ėč(g®įu)áņ(y®Ęn)÷Ē(j®ęn)£¨Ą”(d®įng)ĎB(t®§i)◊‘»Ľ£¨∂ÝĻPńęĄtļņ∑Ň≤ĽŃb£¨ö‚ōěťL(zh®£ng)ļÁ£¨’Ļ¨F(xi®§n)≥Ų°į–ŘúÜ…nĄŇ°ĪĶń™ö(d®≤)Őō√ś√≤°£
Ö«∆Ö÷ģĶńéü≥–Ątłý÷≤”ŕ°įļ£Ň…°™’„Ň…°Ī√}Ĺj(lu®į)°£ňŻ‘ÁńÍ ‹ĹŐ”ŕÖ«≤żīTĶ‹◊”÷T¬ĄŪć°ĘŇňŐžČŘ£¨…ÓĶ√ůĺŹ]°įĹū Į»Žģč°Ī÷ģĺęňŤ°£∆šĻP∑®ĄāĹ°”–Ѷ£¨ĺÄólłĽ”–ĻĚ(ji®¶)◊ŗł–£¨”»…√“‘◊≠۶ĻP“‚ĆĎ√∑÷Ů°£ļůťL(zh®£ng)∆ŕąŐ(zh®™)ĹŐ”ŕ’„Ĺ≠√ņ–g(sh®ī)ĆW(xu®¶)‘ļ£®ĹŮ÷–áÝ(gu®ģ)√ņ‘ļ£©£¨ŇcŇňŐžČŘ°Ę÷Tė∑(l®®)»żĶ»Ļ≤Õ¨ėč(g®įu)Ĺ®Ńň¨F(xi®§n)īķ’„Ň…Ľ®ÝBģčĶńĹŐĆW(xu®¶)ůwŌĶ°£Ö«∆Ö÷ģĶńňá–g(sh®ī)łŁā»(c®®)÷ō°įĻPńęĪĺůw°ĪĶńŐĹňų£¨Źä(qi®Ęng)’{(di®§o)°įĻPĺęńę√Ó°Ī£¨◊∑«ů–ő Ĺ’Z(y®≥)—‘ĶńľÉī‚–‘ŇcĪŪ¨F(xi®§n)Ѷ°£∆š◊ų∆∑»Á°∂īļĻ‚üo(w®≤)Ōř°∑°∂”ńŐmąD°∑Ķ»£¨ėč(g®įu)ąDĺę«…£¨ĻPńęŌīĺö£¨”ŕ∆ĹĶ≠÷–“ä(ji®§n)∆ś»§£¨ůw¨F(xi®§n)≥Ų°į«Ś—Ňž`–„°ĪĶńĆŹ√ņņŪŌŽ°£
÷ĶĶ√◊Ę“‚Ķń «£¨∂Ģ»ňƶ(du®¨)°įĆĎ“‚°ĪĶńņŪĹ‚“ŗ”–≤Óģź°£ņÓŅŗ∂UĶń°įĆĎ“‚°ĪłŁ÷ō°įĆĎ°ĪĶńĄ”(d®įng)◊ų–‘Ňc«ťł––Ż–Ļ£¨ĻP”|Īľ∑Ň£¨ö‚Ą›(sh®¨)Õ‚¬∂£ĽÖ«∆Ö÷ģĶń°įĆĎ“‚°ĪĄtłŁ÷ō°į“‚°ĪĶńļ¨–Ó–‘ŇcÉ»(n®®i)‘ŕŪćő∂£¨ĻP“‚É»(n®®i)ĒŅ£¨”ŗő∂”∆ťL(zh®£ng)°£Ŗ@∑N∑÷“į£¨ľ» «āÄ(g®®)»ňö‚Ŕ|(zh®¨)Ķńůw¨F(xi®§n)£¨“≤ «≤ĽÕ¨éü≥–ůwŌĶňýĆß(d®£o)ŌÚĶńňá–g(sh®ī)»°ŌÚĶń≤Óģź°£

őŚ°ĘģźŃų÷ģ»ż£ļ…ķ√ŁůwÚě(y®§n)Ňcĺę…ŮĪŪŖ_(d®Ę)Ķń ‚Õĺ
ňá–g(sh®ī)ľ“ĶńāÄ(g®®)ůw…ķ√ŁĹõ(j®©ng)Úě(y®§n)£¨◊ÓĹKõQ∂®∆šňá–g(sh®ī)Ķńĺę…ŮłŖ∂»°£ņÓŅŗ∂U“Ľ…ķĹõ(j®©ng)övŅ≤Ņņ£¨‘ÁńÍľ“ōö£¨ļůÕ∂…ŪŅĻ»’£¨‘Ý“Úĺ‹Ňc»’āőļŌ◊ų∂ÝĪĽ≤∂»Ž™z°£Ŗ@–©Ĺõ(j®©ng)övŚĎ‘žŃň∆šĄā’ż≤ĽįĘĶń»ňłŮ£¨“≤ Ļ∆šňá–g(sh®ī)≥šĚM°įļ∆»Ľ÷ģö‚°Ī°£ňŻĻPŌ¬Ķńķó£¨≥£™ö(d®≤)ŃĘ”ŕő£—¬÷ģ…Ō£¨ńŅĻ‚»Áĺś£¨Ōů’ų√Ů◊ŚľĻŃļ£Ľň…ėšÚį÷¶ĪP«ķ£¨»Áżą…ŖÚv‹S£¨‘Ę“‚ą‘(ji®°n)Ūg≤Ľįő°£∆šňá–g(sh®ī) «“Ľ∑N°į”Ę–Ř÷ųŃx°ĪĶń „įl(f®°)£¨ «Ć¶(du®¨)…ķ√ŁŃ¶ŃŅĶń∂YŔĚ°£
Ö«∆Ö÷ģĶń»ň…ķŌŗƶ(du®¨)∆Ĺ∑Ä(w®ßn)£¨ťL(zh®£ng)∆ŕŹń ¬√ņ–g(sh®ī)ĹŐ”ż£¨…ķĽÓ”ŕĹ≠ńŌőń»ň»¶÷–°£∆šňá–g(sh®ī)łŁ∂ŗůw¨F(xi®§n)“Ľ∑N°įőń»ň—Ň Ņ°ĪĶńťeŖm–ńĺ≥°£ňŻ≥£ģčÕ•‘ļ–°ĺį°ĘįłÓ^«ŚĻ©£¨»Á°∂ŇŤĺ’?q®ęng)D°∑°∂≤ŤĺŖąD°∑Ķ»£¨≥šĚM…ķĽÓ«ť»§Ňcőń»ň—Ň»§°£ľī Ļ√ŤņL√∑Őm÷Ůĺ’£¨“≤…Ŕ”–ĪĮĎć÷ģö‚£¨∂Ý∂ŗ“ä(ji®§n)ŐŮĶ≠÷ģňľ°£∆šĺę…ŮĪŪŖ_(d®Ę)łŁĹ”ĹŁāųĹy(t®Įng)őń»ňĶń°į™ö(d®≤)…∆∆š…Ū°Ī£¨◊∑«ů–ńž`Ķńį≤ĆéŇcĆŹ√ņĶń”šźā°£
Ŗ@∑Nĺę…ŮĪŪŖ_(d®Ę)Ķń≤Óģź£¨Ćß(d®£o)÷¬∂Ģ»ň‘ŕÓ}≤ńŖxďŮŇc“‚ĺ≥†I(y®™ng)‘ž…Ōłų”–ā»(c®®)÷ō°£ņÓŅŗ∂U∆ęļ√ļÍīůĒĘ ¬ŇcŌů’ų–‘Ó}≤ń£¨◊∑«ů°įČ—√ņ°Ī£ĽÖ«∆Ö÷ģĄtÁä«ť»’≥£¨ćĺįŇc‘ä(sh®©)“‚ň≤ťg£¨≥Á…–°įÉě(y®≠u)√ņ°Ī°£∂Ģ’ŖĻ≤Õ¨ōSłĽŃňĆĎ“‚Ľ®ÝBģčĶńĪŪ¨F(xi®§n)ĺS∂»£¨ Ļ∆šľ»ń‹≥–›dľ“áÝ(gu®ģ)«ťĎ—£¨“≤ń‹į≤ÓDāÄ(g®®)ůw–ńž`°£

Ńý°ĘĹY(ji®¶)’Z(y®≥)£ļÕ¨‘īģźŃų÷–Ķńöv ∑ÜĘ ĺ
ņÓŅŗ∂UŇcÖ«∆Ö÷ģ£¨™q»Á20 ņľo(j®¨)ĆĎ“‚Ľ®ÝBģčČĮĶń≤ĘĶŔŽp…Ź£¨łý÷≤”ŕĻ≤Õ¨ĶńāųĹy(t®Įng)ÕŃ»ņ£¨Ösĺ`∑Ň≥Ųģź≤ ľä≥ Ķńňá–g(sh®ī)÷ģĽ®°£ňŻāÉĶń°įÕ¨‘ī°Ī£¨ůw¨F(xi®§n)‘ŕƶ(du®¨)őń»ňģčĺę…ŮĶńą‘(ji®°n) ō°Ęƶ(du®¨)÷–őų»ŕļŌĶńť_∑ŇĎB(t®§i)∂»“‘ľįƶ(du®¨)°įāų“∆ń°ĆĎ°ĪĆW(xu®¶)Ńē(x®™)¬∑ŹĹĶń’J(r®®n)Õ¨£Ľ∂Ý°įģźŃų°Ī£¨ĄtĪŪ¨F(xi®§n)ěťĶō”ÚőńĽĮ°Ęéü≥–√}Ĺj(lu®į)Ňc…ķ√ŁůwÚě(y®§n)ňýĆß(d®£o)÷¬ĶńĆŹ√ņö‚Ŕ|(zh®¨)°Ęňá–g(sh®ī)ÔL(f®•ng)łŮŇcĺę…ŮĪŪŖ_(d®Ę)Ķń…ÓŅŐ∑÷“į°£
Ŗ@“Ľ°įÕ¨‘īģźŃų°ĪĶńłŮĺ÷£¨Ĺ“ ĺŃň20 ņľo(j®¨)÷–áÝ(gu®ģ)ģčįl(f®°)’ĻĶńŹÕ(f®ī)Žs–‘Ňc∂ŗė”–‘°£ňŁĪŪ√ų£¨āųĹy(t®Įng)≤Ę∑«Ĺ©ĽĮĶńĹŐól£¨∂Ý «Ņ…“‘ĪĽ≤ĽÕ¨āÄ(g®®)ůw“‘≤ĽÕ¨∑Ĺ Ĺľ§ĽÓŇcřD(zhu®£n)ĽĮĶńĽÓĎB(t®§i)ŔY‘ī°£ņÓŅŗ∂UĶń°į–ŘúÜ°ĪŇcÖ«∆Ö÷ģĶń°į«Ś—Ň°Ī£¨Ļ≤Õ¨ėč(g®įu)≥…ŃňĆĎ“‚Ľ®ÝBģč¨F(xi®§n)īķřD(zhu®£n)–ÕĶńÉ…∑N÷ō“™∑∂ Ĺ£¨ěťļůĀŪ(l®Ęi)’ŖŐŠĻ©ŃňōSłĽĶńňá–g(sh®ī)ÖĘ’’°£

őń’¬◊ų’Ŗ£ļŐJőűŃō£®őŤńęňá–g(sh®ī)Ļ§◊ų “£©








įl(f®°)ĪŪ‘u(p®™ng)’ď ‘u(p®™ng)’ď (3 āÄ(g®®)‘u(p®™ng)’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