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Ǖr(sh��)���x�K�Y

�}�D���K�Y��
�˂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x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ľ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ġ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v��(j��ng)ǧ���꣬�Ƿ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õġ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֮�І���
�W(xu��)���섂�ڡ��K�Yʮ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ˌ�(du��)�K�Y�Ę�(b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Ԋ(sh��)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з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߀ԭ���侫�����硣�҂��@�ŵ��ԸQ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^��(l��)�^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Ʒ�L�ˡ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Ĺ¼ţ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̎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Ľ�Ó�����ڱ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Ȼ�з���(f��)��Ǣ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ζ�عĄ�(l��)�˂��e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Ǵ˼��˵Ĵ𰸣�����չ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ğ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ı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u�����д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Ҳ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Խ��]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ڡ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Ć��(xi��ng)�x��֮�С��v��ͣ�����،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���ժ�x�ԡ��K�Yʮ�v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P�˾W(w��ng)�x��(sh��)��С��(bi��o)�}�龎�����M��ƪ�����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p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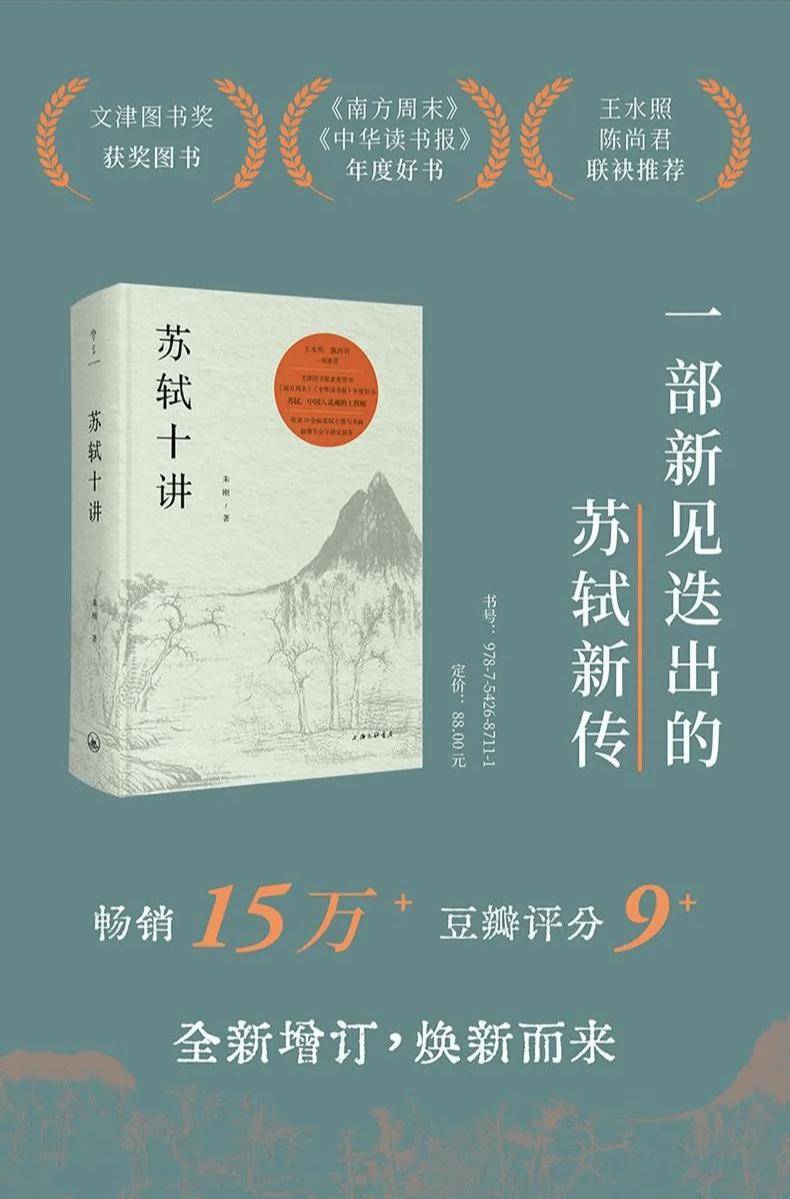
���Ǖr(sh��)���x�K�Y
�� | �섂
��(l��i)Դ | �P�˾W(w��ng)�x��(sh��)
01
�ġ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w����
�K�Y��Ԋ(sh��)�~�Ќ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dz��࣬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Á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B(ni��o)���S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ĸ��Q�w��(l��i)�wȥ���K�Y�ǂ�(g��)�نT��ҲҪ�S��͢�IJ�Dz�܁�(l��i)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һ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܁�(l��i)��ȥ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һ�δ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w�^(gu��)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ô����(l��i)ʲô����Ҳ�S��Щ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ǡ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ꌑ(xi��)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Ē���˿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@�H�H���K�Y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(gu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Ђ�(g��)�K�c(di��n)���҂��ȁ�(l��i)��һ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K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dz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K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ͬ�ˣ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б�Ҫȥ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ͬ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@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λ��ڽ��о���(gu��)Ԫ�꣨1101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꣬�����Hֆ֮�غ��ύu�@�ⱱ�w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꣨���K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ѷ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퍷�֥�e�fԊ(sh��)һ�ס���
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̎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Ǐ�(f��)��ţ̤�fۙ��
��Ը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shu��)�ҮY�ﲻ��ꡣ
�K�Y��(xi��)�˴�Ԋ(sh��)�Ժ������¶�ʮ���վͲ����ڳ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еġ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ҿ϶����Á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ĺ��ϱ��w����
�҂�֪���@һֻ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R�Ͼ�Ҫ�K�Y(ji��)�ó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ǂ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(xi��)�¡���̎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Ǹ�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IJ�ͬ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ஔ(d��ng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ġ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ı��^�н�Ó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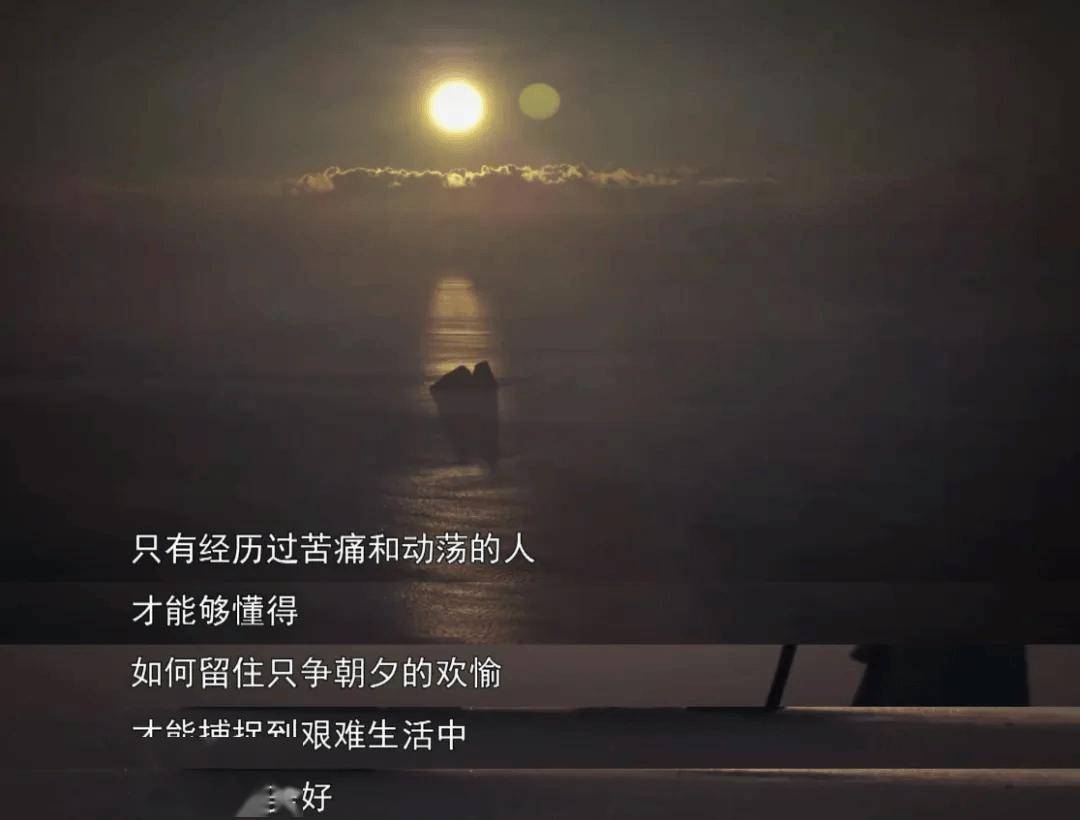
�o(j��)�Ƭ���K�|�¡�
��(d��ng)Ȼ�@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^�y�x�����ˡ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߀�С���ţ̤�fۙ���͡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Ԋ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ֱ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x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U�f(shu��)���@�ӵČ�(xi��)���o�҂����xԊ(sh��)����ɺܴ��ϵK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ٛ(z��ng)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Ō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ӆ���K�Y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У�˸��N�汾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С������¡�һ�Z(y��)У�Ğ顰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У���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Ҳ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
�K�Y��һƪ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(sh��)�^(gu��)�͕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ܵ��ٽ�(j��ng)�^(gu��)��ʮ��ՓԊ(sh��)ϲ�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O��ο�|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r(sh��)Ұ�o(w��)�~(y��)����ȥ���e�T(m��n)��ȸ�_���Ĵ��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r(sh��)��(f��)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ڏV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͕��㡷�ƣ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ಡ���ѽ^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п��^����ƪ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؞��(sh��)֮���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ʮһ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ǽBʥ���꣨1097�����K�Y�H���ڻ�������֥ǰ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ă����K�^(gu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һ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ͽo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^��䛵İ˾����K�^(gu��)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С��Ĵ��ڎ������¡�һ�����K�Y�ں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ͷ�֥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¡����҂���һ�¡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һ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Ώ]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Ԫ�v���꣨1092����
�@�ӣ��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^(gu��)�ǣ�Ԫ�v�����K�Y�ѷ�֥�����顰�¡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^(gu��)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Q(ch��ng)�S��֥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顰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˼�ǡ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H�f(shu��)���ǘ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퍷�֥�e�fԊ(sh��)һ�ס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K�^(gu��)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(l��i)ٛ(z��ng)�跨֥���ı��ϑ�(y��ng)ԓ�ԡ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ʲô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ǰ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ǵ�һ�����@�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t�����Ѳ��ǵ�һ�Σ��@�Ǻ���Ҫ�IJ�e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c��֥֮�g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p����֪�ԣ��Ҳ���ؼ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hu��)�͜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(ji��n)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ɸ�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۵Ľ�����
�@һ�c(di��n)ֵ�Ï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?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K�YԪ�v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�跨֥�ġ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Ώ]ɽ������Ҳ�Ƿ���(f��)ʹ�ã��҂����挢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Ʒ�г��F(xi��n)�þ��l�����京�x��؞鷨֥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ٛ(z��ng)Ԋ(sh��)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҂�?n��i)��м?x��)��Ħ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t�K�Y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B؞�سʬF(xi��n)��һ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�}�ġ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ҬF(xi��n)���ǡ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¡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ʲô�����҂�Ҫ��(du��)�@��һ�l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ͱ�횏��K�Y��һϵ���ı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ĕ�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ú�����˼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ǣ��@Щ�ı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K�Y��һ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
02
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ľS��
�K�Y����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v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H�K䭺͵ܵ��K�H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ծ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ͨ�^(gu��)���e��ԇ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ɴ����ڿ��\(y��n)�ϲ�e�ܴ��K䭿���һ݅�Ӷ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K�H�t�ڼεv���꣨1057����һ�΅��ӿ�ԇ��һ�e�ǿ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ǚW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ֵܾͳɞ�W���ġ��T(m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K�Y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T(m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DZȽ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һ������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�^�К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εv���꣬�K�Y��ĸ�H�����ڼ��l(xi��ng)ü��ȥ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횻ؼҞ�ĸ�H��Т�����˼εv���꣨1060���ٵ����εĖ|���_(k��i)�⸮���ښW�(y��ng)���˵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Hһ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e�е��ƿƿ�ԇ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衰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P�踮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й�?g��u)d���¡��Ĺ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H�͵ܵ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ȥ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Ќ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ɝƳؑ��f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KԊ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ˣ�
������֪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w��̤ѩ�ࡣ
����żȻ��ָצ�����w�Ǐ�(f��)Ӌ(j��)�|����
��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ڟo(w��)��Ҋ(ji��n)�f�}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߀ӛ��·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H˻��
�@��Ԋ(sh��)ǰ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ǡ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ā�(l��i)�v��
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ε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С�Ă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ʎ��̫��Ŀ��g֮�У�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K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ѶU����993��1064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Ʃ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z֮ۙ����ˮ�o(w��)��Ӱ֮�ġ���(l��i)עጴ˾䣬�J(r��n)���K�Y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U�Z(y��)�Ć��l(f��)��
�҂��Ҳ��܃���֮�g�з�YԴ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̶����Ӱ��ѩ�ϵ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`�o(w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f(w��n)���Ԍ�żȻ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ջõĶU����

�o(j��)�Ƭ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K�YȫԊ(sh��)����˼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Ҫ�o(w��)ҕ�@���E��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Ғ���E���mȻ��żȻ���µĺ��E���mȻ���º��E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֪ȥ�����mȻ�B���E����Ҳ���ڕr(sh��)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Нu�uʧȥ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Ե����У�ɮ���ډ����}Ԋ(sh��)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s���ɺ��E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µ��r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ѵܵ܁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@ӛ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Ѻ��K�Y�ă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ƣ����U���ԶU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⣬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ջ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s�����෴���f(shu��)�mȻ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ϵ���ۙҲżȻ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µĺ��EҲ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ֻҪ�й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Ĝ�ܰ���@Ҳ�S���˶U��Ć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
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Ǐ�(f��)Ӌ(j��)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K�Y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_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żȻ�Ե������˻µČ�(sh��)�r�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��@�ӵĸ��܌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m(x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Ԋ(sh��)�~��Ҳ�����جF(xi��n)��ֱ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K�H�ڡ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Ȼ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ľS��
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�K�H�@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ע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о����Ԟ�żֵ���o(w��)̎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أ����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r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ڞ��֮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S��͢��Dz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(l��i)֮�ںεأ��t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S�L(f��ng)�hʎ����ǰ;Ҳ���(m��ng)��һ�㲻���A(y��)Ӌ(j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Ȼ�Dz�����ȫ�A(y��)Ӌ(j��)�����K�Y߀���P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dz����p�Ļʵ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Ӣ���^λ����Ԫ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꣨1066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K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K�H�ٴλ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Т�����g��Ӣ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λ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꣨106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Т���K�Y�ص��|����ӭ���ײҊ(ji��n)һ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ʯ׃����
03
�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ꡱ
��ֵ����ϧ
�@��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�ʯ׃�����Ƿǹ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@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ǰѱ��ε�����˺�ў�ɰ룺֧��׃���ġ����h���ͷ���(du��)�ġ��f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ԭ��ʹ�K�Y�x���˷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֧��ʹ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ڡ����f�h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�ռ��(j��)�˃�(y��u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@��ʹ�K�Y�����x�_(k��i)��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꣨1071���κ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꣨107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꣨107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ڵط��Ϲ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ٵ�����횈�(zh��)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Dz��õģ��ڮ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Щ��й���@Щ��й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ע�⣬�J(r��n)���ǐ�����I�S���㌦(du��)�K�Y���ԏ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ԪԪ�S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ԭ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ʯ��Ԓ�Z(y��)�x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(du��)�ʵ������Z(y��)���ĸ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Ľ��x�e(cu��)λ���o�K�Y����(l��i)һ��(ch��ng)�Ϊz֮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(d��ng)��Ұ�ġ����_(t��i)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Ԫ�S���꣨1079���K�Y�D(zhu��n)�κ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ʮ���¶�ʮ���ղŽ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g��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�Ӎ����ʷ�_(t��i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D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��ɲÔ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s�J(r��n)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ɓ�(j��)��͢�v���C�l(f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(xi��ng)���Ϳ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ɻʵ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؟(z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S�݈F(tu��n)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۵��K�HҲ���H��O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}�ƶ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Ԫ�S���꣨1080�������꣨1084���g���K�Y�H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~��ٴ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ȣ�
ȱ����ͩ��©���˳��o��
�l(shu��)Ҋ(ji��n)���˪�(d��)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
�@���s���^���кޟo(w��)��ʡ��
���M��֦���ϗ�����įɳ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(xi��)�Լ�����ԭ��(l��i)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S��͢��Dz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�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X(ju��)�ùѼ�į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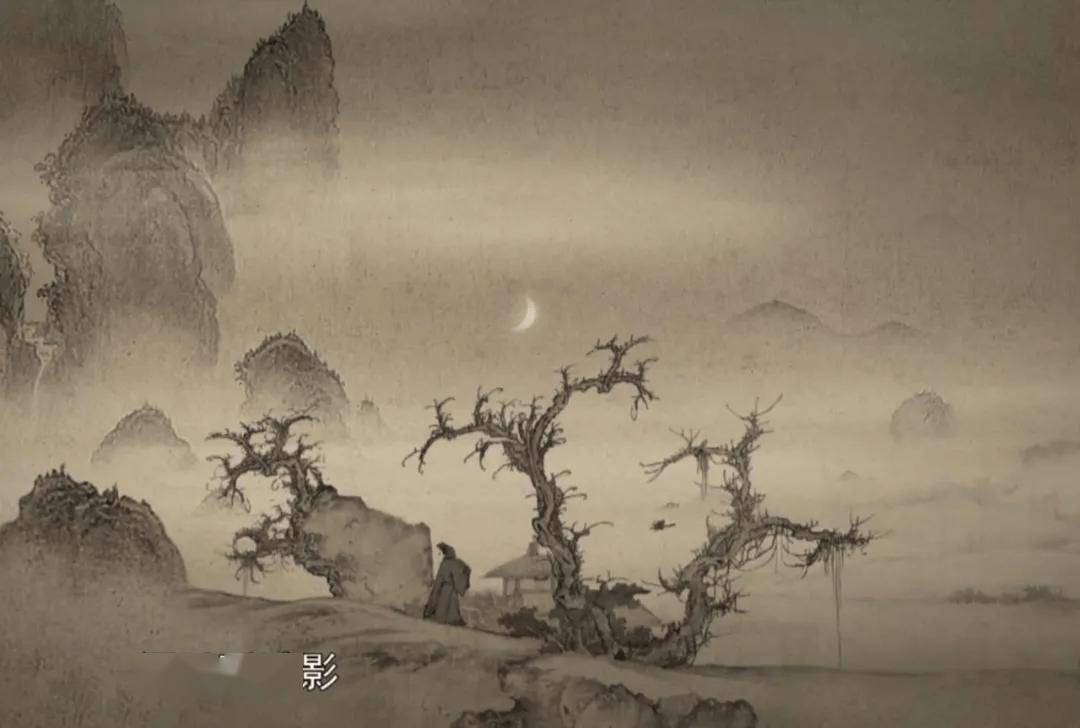
�o(j��)�Ƭ���K�|�¡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֦���ϗ�������Ըͣ�ڼ�į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Լ��ė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w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c��ȫ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S�L(f��ng)�hʎ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ܲ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Hֆ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w�Ե�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H�ӵĕr(sh��)��?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r(sh��)�ڸ�����
�K�Y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�װ����ˌ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䣺
�|�L(f��ng)δ����|�T(m��n)�����R߀��ȥ�q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紺��(m��ng)�˟o(w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ባ�Ұ���n�һЦ����
�Ѽs�����˕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x���л꡷��
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ͬ�ĕr(sh��)�g���s��ͬ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ͬ�ĵ��c(di��n)�ە�(hu��)���Ⱦƌ�(xi��)Ԋ(sh��)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H�ӾͲ��옷(l��)���@�(xi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B(ni��o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(hu��)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Ǖ�(hu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ģ�һ��һ�ȵ���ͬ�ĵ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n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(l��i)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ɵ����侳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żȻ�Բ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ǁ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cϲ��(��i)�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ش��� (t��ng)���ڳ�͢���˻����IJŕ�(hu��)��̎Ư����
�@��(g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֡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ʮ�ךq���K�Y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?ji��n)��ͬ�����A(y��)��ʵە�(hu��)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ܞ��˻����ľʹ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đB(t��i)ȥ�m��(y��ng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H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K�Y���˻����IJ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S�ݽY(ji��)����Ԫ�S���꣨108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x�_(k��i)�S�ݣ���ȥ���ݾ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ľӳ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Ԫ�S���꣨1085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λ��̫��̫����� 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R��ȡ��f�h���نT���K�YҲ��ʮһ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ٻؾ��ǡ�Ԫ�vԪ�꣨1086���κ��W(xu��)ʿ�����ˡ�Ԫ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ǼѾ�����Ҳ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ʧȥ�����ֱ�� (t��ng)���ڳ�͢�IJ�Dz����̎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롰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Ԫ�v���꣨1089�����K�Y�ٴ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)��֪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š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Σ��@�DZ���͢��Dz��ͬһ��(g��)�ط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εĽ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żȻ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C��
��̎�����żȻ����(m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A�
߀��(l��i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Ԋ(sh��)��](m��i)�Ќ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䡰��̎���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þ��ǡ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x��ֱ��(xi��)��̫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w��̫��Ŀ��g�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MżȻ����ͬ��(m��ng)���](m��i)�и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Ė|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g���s�ğo(w��)Ϣ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˴˿����Ķ��ǝM�^�װl(f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п�֮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K�Y�mȻ�](m��i)�б��@�����x�߷����ܸе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K�YҲ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ԓQһ��(g��)�Ƕȁ�(l��i)���@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С�Ă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˾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hʎ������Ȼ�܉��ط����Ǻ�(ji��n)ֱ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E����ɿ�ο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Ԋ(sh��)�ĺ�ɾ�Ť�D(zhu��n)�˱��^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顰�طꡱ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ط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ܰ�Ě�գ��(q��)���˿�Į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
ʮ����ǰ���K�Y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ͬ�ӵ��龰�����һ�γ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ǰ���·�һ���ƓP(y��ng)��(l��)���е����}�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طꡱ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E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Ҳ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E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
���B(ni��o)һ��һ�ȵ�ͬһ��(g��)�ط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Ҳ�ǡ��طꡱ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Ҳ�С��طꡱ�����Ǹ�ֵ��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аl(f��)����һ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͕�(hu��)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ܶ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ϧ�Ė|�����҂��x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x���@�ӵă�(n��i)�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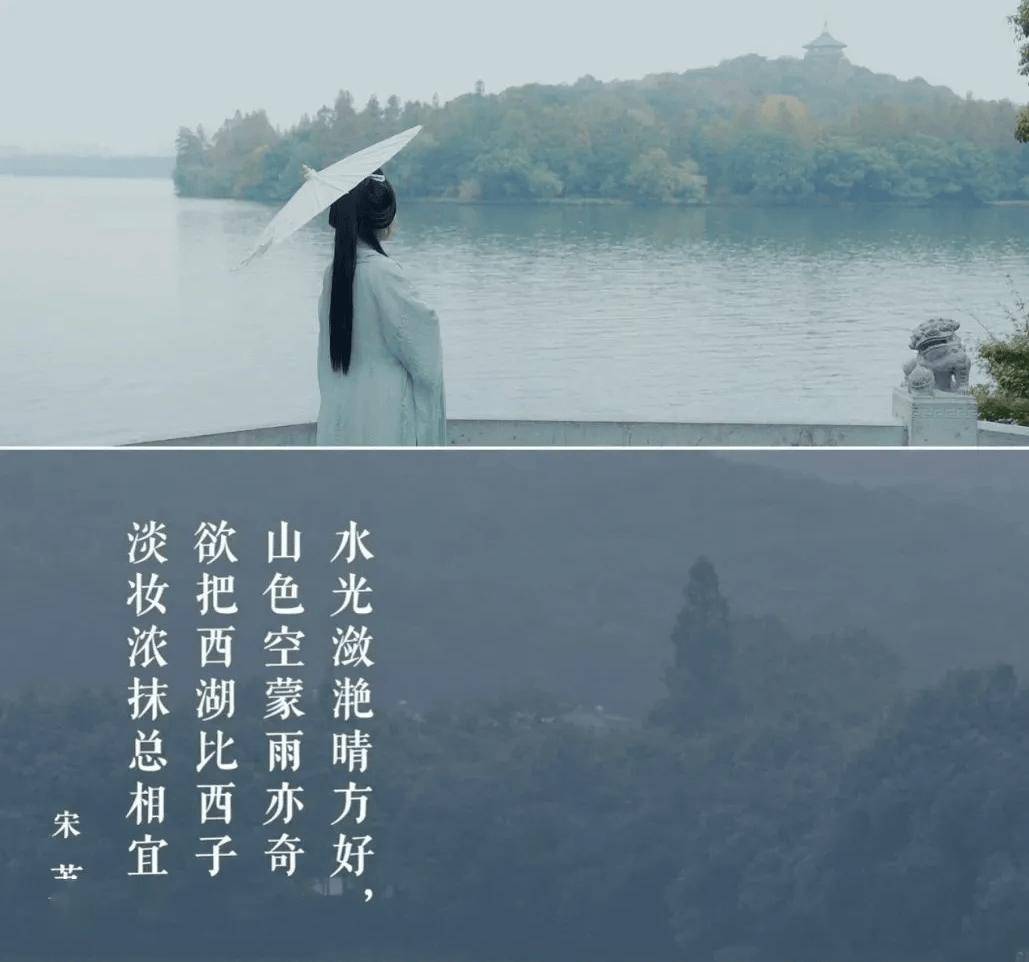
�Cˇ���I�I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K�Y�x��?x��)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v���꣨1091��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ĵܵ��K�H�ѽ�(j��ng)�@�ø��ߵĹ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ˈ�(zh��)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ι����Ⱥ��ڝ}�ݡ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ݵȵ�?f��)?d��n)��֪�ݣ����gҲ���Ў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@�õ���߹��Ƕ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W(xu��)ʿ���Y���Е�(sh��)���@�x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֮�b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ʷ���ġ��K�Y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ܮ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z����
���^(gu��)�K�Y����;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һ(li��n)���С�һ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](m��i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˾�R��ȶ��[�ò�̫�_(k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^(gu��)�ط��ٵĺ������}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Ђ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Hֆ�����ݣ�߀���Ђ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04
���F(tu��n)�F(tu��n)��ĥţ������̤�?��i)E��
���طꡱ��ϲ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Dzɢ��̎żȻ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ϲ���R�ϱ���һ�N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Ԫ�v���꣨1092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Ώ]ɽ���У�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ţ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ϧ���F(tu��n)�F(tu��n)��ĥţ������̤�?��i)E���M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c�~(y��)�B(n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Ō��ߏ]����Ӌ(j��)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̎�l(shu��)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f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̎�L���ҡ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ָԪ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K�Y�ĺ���֪�ݱ��ٻ����ֳ�֪�}�ݣ��Ɠ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K�Y��ʮ���ߚq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꣬�u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½�(j��ng)�v֮�أ��R�ϳ��؏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m�С��طꡱ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طꡱ�ö������s�q���D(zhu��n)ĥ֮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̤�?��i)E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wĽ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@�η���ɮ�˿��ǵ�̎����ÿ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Ҫȥһ��(g��)�µĵط����@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Ҫȥ�]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̎�l(shu��)�ܱء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ľ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A(y��)����ֻ�á��F(tu��n)�F(tu��n)��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ش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
�X(qi��n)�R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ĥ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֮�x(ch��ng)����ĥ֮�H��ĥ��֮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е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U�?zhu��n)��f(shu��)�@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̰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ѭ�������ع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Ó�o(w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˼��
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Á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ĥ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෴��ǰ�߿��ڵ�̎żȻ�����߄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؏�(f��)�o(w��)Ȥ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X(ju��)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Ї@�˾���ֵ��żȻ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�;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Ğ�Ї@�˾���ֵ���؏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@һ�D(zhu��n)׃�У��e���˺��ص�����醚v�;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
��ѩ����צ��֮���а�ʾ���ǂ�(g��)̫��Ŀ��g���ڡ�ĥ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׃��̫С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r(sh��)���ս��Q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r(sh��)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С�����ʹ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ν��R���K�Y�^�ϵ��Hֆ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s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δ���ĎX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㌎�f(shu��)��ֵ�Úg�c����

Ԓ�����K�̴��ԡ�
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ص�����퍷�֥�e�fԊ(sh��)һ�ס���
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̎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Ǐ�(f��)��ţ̤�fۙ��
��Ը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shu��)�ҮY�ﲻ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K�Y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֮һ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˼���Ŀ��Y(ji��)��
�䡰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ꡰѩ����צ��֮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Ѵ���ͬ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@�β����S�L(f��ng)�h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(j��ng)�h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w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w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H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քe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һ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ρ�(l��i)�w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˽��K�YԊ(sh��)�~��(du��)�ڡ������ĕ�(sh��)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Ԋ(sh��)�еġ��w�����϶�Ҳ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~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ꡰѩ����צ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ֵ��żȻ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w���ֽ�ȥ����
�ξ䡰��ţ̤�fۙ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ĥ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ν�(j��ng)�ˡ���^��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ˡ��Ǐ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є[Ó������̤�?��i)E��֮ʹ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ľִٺ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؏�(f��)ѭ�h(hu��n)Ҳ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(du��)��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֮��Ŀ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ԭ��һ�����?l��i)�Ĺ�ͬ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x���w�Y(ji��)���ˡ��¡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K�Y����˼���Ě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ȫ�جF(xi��n)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Ԋ(sh��)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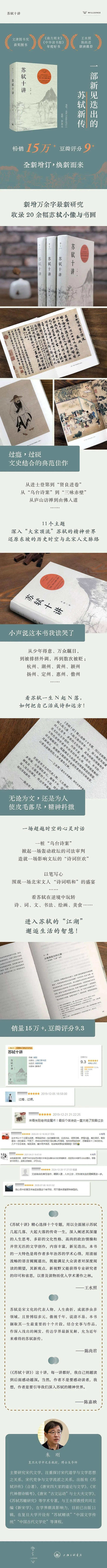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2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